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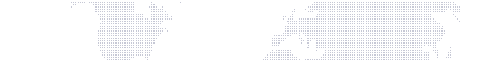
| | 网站首页 | 文章中心 | 学术动态 | 资料下载 | 建议留言 | 文化论坛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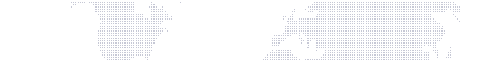 |
| 您现在的位置: 文化中国 >> 文章中心 >> 文化前沿 >> 文化现象 >> 文章正文 |
|
|||||
| 身体形象与情色文学:性别议题讨论 | |||||
| 作者:陈玉珈、… 文章来源:南华出版所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3-27 | |||||
|
壹、前言 基本上,〈身体形象与情色文学:性别议题讨论〉这个题目可讨论的面向相当多,本组也很希望面面俱到。但是,由于资料收集上的限制,本组将重心偏向在情色文学作品的介绍上,并稍微提到同志文学,而选择性地略过情色文学的查禁史,以及所谓的网络情色文学。
什么是情色文学?这似乎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既然我们要谈情色文学,还是得先试着解释它,至少得了解一些学者的说法。 提到「情色」二字,相信许多人会很快地联想到另一个词──「色情」,并且提出疑问:情色与色情,有何差异?或者,两者根本是相同的?在一般人的感觉上,「情色」一词显然比「色情」来得雅,「情色文学」又比「色情文学」来得高级,但情色与色情如果真的有所不同,它们的差异又是什么? 我们从资料上发现,「情色」一词显然是台湾晚近才盛行的新词,中国大陆并无此用法。是故,为了厘清「情色」与「色情」的关系,我们试图从英语中找寻线索。 在英语中,有Erotica & Pornography这两个意义相近、但其实有所分别的词。Erotica一词源自希腊神话中的爱神Eros,泛指一切和性爱或性欲有关的感觉和事物。Pornography一字有两个主要涵义,一是按照其希腊文字根之义(porne-harlot,graphos-writing),指一切有关妓女的生活与行为之描述。二是指一切猥亵淫秽的文字或影像作品。(赖守正,1997a)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把Erotica与「情色」对照,pornography与「色情」对照。 关于Erotica与Pornography的不同,廖炳惠教授将之解释为「唯美色情」与「暴力色情」。前者将性器官视作身体与另一个身体达到圆满沟通与解放的媒介,因此把作爱与爱抚钜细靡遗的描绘,但始终保持身体的神秘、美妙,而且往往在色情之中透露出某种意义。后者是刻意夸张性能力与器官,表达出某种性别(通常是男性)的滥用力量,去侵犯、强暴、侮辱、丑化另一个身体。(廖炳惠,1989) 此外,有些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认为Pornography代表的是男人对女人的主宰与暴力,对女体的物化与剥削。而Erotica则是歌颂人皆有之的肉体情欲,但少了对女性的歧视。(赖守正,1997a) 桑塔格(Susan 所以,色情与情色、Erotica&Pornography,真的能做一刀切断的二分法吗?有些反查禁的女性主义者,就曾讽刺地指出:「使我『性』起的是情色,使你『性』起的就是色情。」英国女作家安琪拉.卡特(Angela Carter)更点明:「所谓情色,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色情罢了。」(赖守正,1997a) 所以,事实上,不论是情色或色情、唯美色情或暴力色情、Erotica与Pornography,都是很难以明确界分的。它们之间,有个灰色模糊地带,而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处于其中。有些我们今日认为的情色文学经典,如D.H.Lawrence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或《金瓶梅》,在过去都是禁书、无法登大雅之堂的淫秽之书。但,经过时代与观念的转变,它们却因其文学价值而被称诵。 如1959年,英国政府通过「色情刊物法」,明禁色情但保护经典文学。1960年根据此法,《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判定不涉色情,才得以在英国本土以全貌出版。我们今日看劳伦斯当时之遭遇,相对于今时的鼎盛文名,唯有感叹人类社会之道德尺度实在是特定时空之下的产物,绝不足以放诸四海皆准。(宋美王华,1980) 所以严格说来,情色/色情根本不是个客观的存在,一件作品构不构成情色/色情,重点不在于客观的「影像」(image),而主要在于观者主观的想象(imagination)。(赖守正,1997a) 因此,我们并不打算为情色文学下一百分之百的明确定义(实际上,也不太可能),只提出资料上不同的看法,做一些整理归纳。而我们在报告中谈到的一些文本,也许亦游走在情色与色情之间,难以下定论,但至少它们都是具有某些代表性、时代意义,或已被公认为情色文学经典者。
参、中国古代情色文学的发展概况 在古代社会中,由于重视种族繁衍,再加上当时礼教文明开始萌芽,甚或完全阙如,基本上人们对性的态度是相当坦荡自然的。(赖守正,1997a) 在《易经》〈系辞下〉中,就有「男女媾精,万物化生」之句;《礼记》〈礼运篇〉亦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即使如此,在中国文学中关于性爱方面的描述一直是比较婉约含蓄、暧昧隐喻的,直至隋唐后,才形成较具体的情色文学,到明朝时更达到一个颠峰。以下略述中国古代情色文学的发展。 先秦两汉主要的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汉赋、古诗等,都极少情色的成分,顶多是恋爱心理的描述。但在正统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特殊的文类可提出来略作介绍,即是所谓的「房中术」书籍。 尤其是汉初倡黄老之学,行无为而治,故对性方面的问题并不很忌讳,如在先秦就有专讲男女性交之道的房中术,自汉特盛。现见《汉书.艺文志》所载房中术的书就有八种,如《容成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等。(孙琴安)到了魏晋南北朝,所谓的房中术,竟已发展到十几个学派,提出了一百多种方法和技巧。 到了唐朝,由于文学创作上比较自由,对性的表现也没有严格的限制,因此出现了一些较明显的情色文学。例如,白居易之弟白行简所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在此赋中,他先从男女两性的生理结构谈起,继而谈到各自的性发育和成熟的过程,然后由此谈到性意识和性欲念的萌动和产生,讲男婚女嫁,并对男女新婚之夜的性交作了详细具体的描写。(孙琴安)现今读之,仍觉其描述十分详细大胆。 另外,张鷟所写的传奇小说《游仙窟》也堪称是唐朝情色文学的代表之一。这篇传奇小说的内容,是以第一人称自叙其奉使河原,路过积石山,进入神仙窟,与崔十娘盘桓一宵之艳事,对两性有坦率大胆之描写。此书于当时传至日本,对日本文坛颇有影响。日本学者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称之为日本第一淫书。(叶庆炳,1987) 宋朝较具代表性的情色文学,当属秦醇所撰之《赵飞燕别传》。内容是关于赵飞燕及其妹赵合德如何进宫且得宠,服侍汉成帝,同时反应了当时汉宫中的淫乱生活。其中对于女子裸体的描写,虽不如明清通俗小说那样描写细腻,但还是颇具性感和挑逗的。(孙琴安,1995) 到了元朝,虽然没有较惊世骇俗的情色文学作品,但主要的文体「散曲」中,即可见到较具体的情欲描述。另外,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也可见到情色的成分。 明朝可说是中国古代情色文学发展的颠峰,一方面,是由于明朝盛行的文体——小说、戏剧,适合做详细的白描;一方面,亦跟当时的政治、社会、思想有关。 此时期较著名的情色小说,有以一般市井小民作为主角的,有《疯婆子传》、《绣榻野史》、《怡情阵》、《春灯迷史》、《浪史》等。这些作品中对性的描述,都极为大胆详尽。 另外,有专以宫廷艳史为题材的,如描述武则天荒淫性生活的《如意君传》、《浓情快史》;描述赵飞燕、赵合德姐妹性生活的《昭阳趣史》。 尚有描述同性性爱的《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尤其是《龙阳逸史》,在明代男风盛况与小官(以今之用语解释,即为男妓)生活的反映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如男风盛行,小官的生意甚至压过娼馆,逼使娼馆关门大吉。 另外,著名的三言二拍──冯梦龙所纂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及凌蒙初所撰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中,都有许多男女交欢或同性性爱的描述。 而论到明代的情色文学绝不可不提的,便是中国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金瓶梅》以生动活泼的笔触,无所忌讳地大量描述性行为,写西门庆的纵欲无度(据统计,全书中和西门庆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共有二十人,此外尚有同性性关系的描写)和性虐待倾向,写潘金莲在性欲上的贪得无厌,直教人瞠目结舌。它也算是中国古代情色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 到了清初,较具代表性的情色文学作品应是《肉蒲团》。《肉蒲团》的故事内容,是描述主人翁未央生虽有妻室,但为色欲所驱,想尝试天下众美的滋味,而离家出走后的过程,到最后自割阳具,一心奉佛。此书中对于性爱的描绘具有极大的挑逗性和诱惑力,在人物上的塑造也很鲜明。 清末民初,较为知名的情色文学作品,则是《品花宝鉴》(陈森撰)以及《留东外史》。前者有大量同性性行为描写,后者在当时以淫书驰名,主要是描述中国留日学生的放荡纵欲生活。
肆、从中国古典情色文学看身体形象与两性 一、前言 中国周代以后,其实在《诗经》中的记载可以发现当时的社会,男女间的交往是开放而自由的,在初民社会中,性生活是具有超自然的巫术性格般,古代中国,男女匹配象征着天地阴阳交欢。春秋战国之际,礼乐崩而郑声行,许多女乐、管仲女闾(公妓)的设置、娈童之嬖盛行,所以节制性欲的说法纷起;在汉代以后,中国便将性与医理、天象结合,强调合时合节的重要性,要求将人体与自然、德性统合并系统化(例如:八卦),此时社会中性交一事除了传宗接代外,更藉此培精(男)、调息气血(女),并重儒家伦理及礼法。宋代对性的态度仍很宽容,例如,当时还流传着《入药镜》、《邓云子》、《五牙导引元精经》……等教科书,但宋代以后,贞节观念就集中在对处女的要求;而到了元代,就对儒家礼法特别强调,此后,中国妇女行为举止的端庄娴淑,成了社会的常态;但到了明代,才是中国关于男女交往、社会风气及性观变迁的重要转折时期,从司马光请禁「妇女裸体相扑」一事即可知道,社会中对于男女之防及将妇女正位于内的仪礼规范,比以往要求严苛,房中术(房中术的意义于对女性欲望满足的达成,并赋予男性养生的意义。)于床第间依然施行,但已不如以往般自由而公开地流通了;清代以后,中国人陷于暴露任何关涉性事项的恐惧中,这种对性的恐惧态度持续了四百年,迄今不衰。(翟本瑞,1999a) 荷兰高佩罗认为,中国古代的性观随着明代的衰亡而告中止,起而代之的是视性为不自然、污灭、变态的看法,使后人失察于中国传统中对性固有的健康、自然的态度。(高罗佩,1991)所以男女之事,成了在学术研究时的禁地,例如:在令文风编译社翻译金赛的《女性性行为》一书时,虽号称「原书翻译本」,但却出现了下列说明:(金赛,1954)「……原书的研究过份重于生理和生物因素,有时未免忽视了伦理和社会的现实观点,关于这一点,本社在翻译的时候,对于那些过份暴露女人性行为的地方不免有所删节,此非译者之原意,实乃基于我国数千年社会传统而应有的保留态度,敬希读者见谅是幸!」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对「性」的避讳,能够收集的资料自然相当有限。 随着时代的变迁及西化的结果,使近代台湾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自由化,七O年代以来,在《花花公子》、《阁楼》的带动下,及性解放运动与女权主义的兴起,使性与色情成为商品化产物,性商品的暴增、公开;性行为模式的改变,及摆脱生育繁殖为主的观念;性享乐的满足、愉悦,一跃而为情欲表现的重要符码。这些以情欲为主体的论述,连向为禁忌或边缘的同性恋也扩散形成具诱惑力的性文化。九O年代的台湾文学已大胆突破情色的禁区,情色课题成为现今台湾最热门的文化课题。
二、中国第一篇情色文学 「……于是寝具既设,服玩珍奇,金鉔熏香,黼帐低垂。裀褥重陈,角枕横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司马相如《美人赋》 刘大杰将这篇文章喻为「中国第一篇色情文学」指其「用最细密的描写,大胆的态度,以及清丽洁白的文句,去表现一个色情狂的女子。」 但若看其汉代的时代精神,我们若非用后世礼教男女大防的标准视之,其实也是常态现象。(刘大杰,1962)
三、身体形象 (一)春宫图 中国文化在明代以前,对性的相关事务上的观念是自然、活泼、健康而开放的,因此在中国的春宫画中,便可对于中国文化中对性所表述出来的意象及标准。在中国春宫画中所出现的女人并不是不重爱欲的描写,而重点毋宁在于中国传统爱欲的表现方式与欧美、日本有所不同。由于传统春宫画的观赏角度和现代有所不同,所以很难用现在的标准来断其优劣。但春宫画的目的在于愉情及催情,它预设了观众情欲的参与,春宫画本身是观众潜意识中情欲的投射。(翟本瑞,1999b) 由于西化的影响,现今许多对于身体的审美观,都来自美国的观点,但是中国人(东方人)的形体和美国(西方人或欧美)的形体是有很大视觉上及生理上的差距的,但日本就在这方面,形塑了和西方不同的展现模式,是比较适合东方的,同时却又和中国文化有所差异。因此,思想与行为模式上的西化,不见得适用于中国社会文化,福田和彦在《中国春宫画》中指出: 中国秘戏图并不如日本的春画露骨,尤其在性器的描绘上,也不如日本夸张。在中国的春宫画上,很少有关阴毛的描写,而且大部份的少女都是无毛、缠足、柳腰又娇弱的形态,彷佛无毛与缠足,即是美女的象征。也就是说,在中国春宫画里出现的女人,都是中国男性的理想偶像。不似日本的春宫画,着重爱欲的描写……。
画中人以才子佳人为主,故男则清秀,女则美艳,其式虽多变化,不背情理,和悦之色现于纸上。古画之病在少曲线美,妇女肢体往往瘦削不堪;此画妙在圆姿替月,盛妆丰容,凡亭台楼阁,花草景致,极求精美。
到了十九世纪,东、西方接触日益频繁,不论是在民主、法制、人权……等观念,在情欲表达上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在春宫图的表达手法上已有所不同,身材丰满、乳房圆润、肩宽肾耸、男女对视男女对视、性器官的交合,成为视觉重点,神情的挑逗神态、拥吻、抚摸乳房……等,都显然受西方影响,这些在传统春宫画中很少见过。(翟本瑞,1999b)
(二)古典文学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中,女性缠小脚成了社会评断女性地位及美感优劣的标准,除了稍后在文中将剖析的女性阶级及父权主义外,更显示了男性及当时社会对于「美」的定义,不论是在中国传统春宫图中或是古典文学里,都在在强调了传统女性缠小脚的重要性。福田和彦曾指出: 缠足的女性走路时,把重心放在脚根,以致身体轻摆;她们无法走远路,外出时必须乘坐轿子或马车,与上了锁炼的家畜并无两样。据说缠足还兼具增进闰房之乐的功效,由于缠足的女性走路时多半借助腰力,使腰部肌肉发达,同时女性的括肌收缩,阴阜的肌肉丰满,可使男性获得极大的满足。 李渔在《笠翁偶集》中曾提及:「其用维何?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此用之在夜者也。」(翟本瑞,1999a)如同,在丁乃非所撰写的《秋千.脚带.红睡鞋》一文中,就重新解读了中国古典文学《金瓶梅》,其中潘金莲即以「三寸金莲」闻名于社会中,而《金瓶梅》的全部叙述也可以说是全部专注于「脚上」-潘金莲的缠足上。如同,在《金瓶梅词话》三回第七十五页中所写到潘金莲第一次被安排与西门庆在她隔壁王婆家的会面。王婆精练地教导西门庆如何「勾引」这个妇人的十个步骤。根据王婆的说法,这第十步重要的招式就是技巧地拂落一双筋到桌下,落到金莲脚旁,然后借机在拾筋时,在她脚上-「金莲」上捏一捏,如果她哭闹起来,则此事便收了,若是她不做声,则「她必然有意」。由此可见,脚(「金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禁忌的、是隐私的、是审美的标准。
再看《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和丫头惠莲交往的情节里,由于惠莲比潘金莲的脚还要小,年纪也小了两岁,加上强烈的企图心,因此和西门庆便勾搭了上,从其中一段对话,也可以看出小脚在当时女性乐于炫耀及男性的欣赏:(西门庆道)「到明日替你买几钱的各色鞋面,谁知你比你五娘(潘金莲)脚儿还小。」(惠莲道)「拿甚么比他(潘金莲)!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试了试,还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小,只是鞋样子周正才好!」张竹坡曾在眉批中仔细数过鞋字出现的次数,共有七十九次。
就生理结构上,中国人属于蒙古利亚种,而蒙古种的妇女通常阴蒂的发育上,未若他种族肥厚,是以中国人嫌恶过大的阴蒂。在生理结构上的其它差异,会配合在文化上的其它差异,产生长期而持续的效果。例如,缠足使得着力落在脚根,促成曲线的隐藏以及括约肌收缩、阴阜丰满等特殊生理变化,这与西方着高跟鞋,力量置于脚尖,促使胸突肾翘、三围毕现,实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与审美标准。(翟本瑞,1999a)
四、父权主义看两性关系 (一)从属关系 不论传统的中国社会或现今的时代脉流里,异性从来就不曾属于同一阶级。在文化价值上,「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1]「从」的概念,赋予了男性上位的权力正当性。「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构筑了男/女、主/从、上/下的性别关系想象。透过各种社会控制的手段(礼法、教育、婚姻……),使得男性得以独占优势,确定女性卑下辛劳的角色形象,点明了女性的成就必须寄托于为男性服务上。《莺莺传》中,莺莺对于张生的拋弃,「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因其宜矣,愚不敢恨。」只自哀其僻陋,未指责张生的无情,实归因于性别角色上的要求,显见了性别上的。 从「从属关系」和「地位/阶级」再来看《金瓶梅词话》二十五回打秋千一段:清明前夕,在西门庆宅院的花园中,接近潘金莲和李瓶儿房间的地方,搭起了一架秋千。自此之后,宅中的女眷(包括月娘、五个姨太太、女儿和受宠的婢女们)便在西门庆不在家时,打秋千作乐。
(二)贞节情操 同时,在妇女地位方面,唐代有一本重要的女教书《女论语》,即说明了当代对妇女的要求,例:《女论语》守节一章即有「有客在户,莫出厅堂,不异私语,莫起淫言。」一般人心中有传统浓厚的贞节观念。「俄而红娘捧崔氏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之端庄,不复同矣。」-《莺莺传》「自献」以贞慎的道德观之,是相当轻佻不端庄的,莺莺缄报之辞也说明:「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没永恨,含叹何言!」女性身体并未获得真正的解放,甚至因对男性道德要求的降低,以不同型式增强对女性的压迫。统治者的极权控制更具体反射在对身体的控制上;对人民的意识型态(不事二姓)期待,也落实于身体的要求上。(黄暄,2000年) 《玉房秘诀》提到「房术为利器,不可假人,不可令女性知之……女人自有不战而胜,以静制动的手段」。男性对女性身体不可掌控的焦虑表露无遗,女性身体的生理诱惑力,使男性产生又爱又怕的矛盾情绪。因此「贞节」便是以身体实践道德上的围堵,全面地将女性的身体置于控制下,透过道德论述的发言权,宰制女性的身体意识;因此,守贞要求,是将女体物化后,男性占有终极欲望(完全拥有)的展现。女性在此成标明身分的消费符号,以对女性的拥有,满足了男性符号消费的竞争,也使得女性在被拥有的过程中,失却其主体性。(黄暄,2000年)
(三)男性对「拒绝」的认知 在《莺莺传》中即可看见,莺莺在这父权主义所建构而成的社会中,所承受的压力(例:举止矜持)及内心却又充满矛盾的心态。例如:<明月三五夜>所言:「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待」与「迎」所表现对异性身体的想望,莺莺因感情而突破身体关系的限制,证成了自我的主体,虽然中国向来都预设了女性拒绝的义务(事实上莺莺基于道德的限制也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元禛续<会真诗>中则提到「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这句话又为女性的拒绝作了解释,实为男性自我中心的世界里,对女性自主意识从未认知过,让女性的拒绝又成了男性理所当然的侵犯借口,女性身体自主意思表示与男性欲望的矛盾,使其不愿接受主体意识表述,不能接受反抗与拒绝的主体意识。(黄暄,2000年) 元稹的续张生<会真诗>,道: 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居绮丛登床居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佣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 这样的论述方式,避免了女子的主动性的可能(女子的主动性让男子有所感应的可能),将女子置于被观看,无法作为的客体地位上,透过阅读让女性身体成社会发挥情色意识的场域,女子柔弱与迷乱的描述,则满足了男性于性行为的主体地位想象。(黄暄,2000年)
(四)以身相许观 另外,中国传统父权中心的压抑下,使得女子无才便是德,而建构女子拥有的只有身体的意识形态,更将身体物化,使传统女性将「以身相许」视为理所当然尔,如同在《莺莺传》中,莺莺就曾说:「兄之恩,活我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使以护人之乱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
(五)性暴力(性虐待) 「我把这小淫妇,不看世界面上,就昝死了」这段话出自《金瓶梅》中西门庆为了纠正金莲对其他妻妾的放肆,所挌下的要胁,这威胁有着「强暴」的预警,因此出现了之后西门庆和金莲两人玩着投壸的游戏,直到金莲略有醉意,决定要在葡萄架下小睡一会儿。当西门庆到一旁去小解时, 妇人又在架儿底下,铺设凉簟枕衾停当,脱的上下没条丝,仰卧于衽席之上,脚下穿著大红鞋儿,手弄白纱扇儿摇凉。西门庆走来,看见怎不触动淫心。于是乘着酒兴,亦脱去上下衣,坐在一凉墩上。先将脚指挑弄其花心,挑的淫津流出,如蜗之吐涎;一面又将妇人红绣花鞋儿,摘取下来戏,把他两条脚带解下来,拴其双足,吊在两边萄架儿上如金龙探爪相似。(《金瓶梅词话》,二十七回,页四O七) 这段文字是西门庆在玩弄金莲身体各部位,一个必须处罚似的「对付」的东西,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将愤怒/欲求的情绪不断地被玩泄出来,只为了显示西门庆自己才是一家的主人。而这段论述的焦点固定在红鞋、小脚、脚带和它们的功用上。西门庆用他的脚去挑弄「花心」,污弄着女人的阴核;在中国身体观的秩序中,脚是低下而不净的的部位,恰与支配全身、顶天的头部相对。而女人的小脚之所以迷人,正是因为那是身体的末端,还是特别经过加工、变形的末端,散发出因长期里缠而造成的特殊腐味;这种迷惑凝聚了阳物父权体系对女性「事物」最深的矛盾和恨/惧。(丁乃非)而且,在这些细节中还包括了红鞋、脚带和被放入复又取出阴道的李子,以及它们所缝合串连的死亡与性爱、性交与牺牲处死,揭示了西门庆对金莲的处罚,而他处罚的方式正是透过「性」的技巧,以致于「昝死她」,透过重复的性折磨来纠正潘金莲的不当行为及侵犯,透过这样类似的性暴力,来使对方身体受伤而达到处罚的效果。
(六)男女禁欲大不同 在性欲望方面,虽然不分性别地被要求节制,但就其社会意义却有极大的差异。就男性而言,性行为上的节制是为了证成精神上的更生与自我道德操持,抗拒欲望是身体与心灵上的「锻炼」;就女性而言,却是道德彰显的手段,是避免危乱秩序的机制。(黄暄,2000年)
五、跳脱历史看现代两性之间 时代在改变,性别/情欲的关系愈形复杂,西方常见的肛交、性变态、恋物癖、恋童癖、同性恋、暴露狂、……等现象,在中国古代史书中多少有所着墨,但由于传统的情欲标准有所不同,对性的压抑主要只有在公开场合,在私底下没有太多限制,所以这些反常性行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极为少见。 在中国传统情色文学中所阐述的性别议题,成为新时代的现在,在女性主义、同性恋…等积极开女性解放和主体意识建构下,将性别议题导向更不具规范束缚的型态;如:萧红、庐隐、白薇、胡晓真、李昂(《迷园》)…等作家也努力解构女性与父权制度之共谋机制的议题,企图重新建立起历史纵深的架构,以性别觉醒中心的运动重谈男女平等。 以邱贵芬的<性别/权力/殖民论述:乡土文学中的去势男人>为例,即成功结合女性主义与后殖民论述。而刘亮雅、朱天文(作品如:《荒人手记》、《世纪末的华丽》)……等人,也以前卫的女性主义自期,但却也在作品中呈现保守的年龄和族群危机,并缅怀父权价值,从过程中探讨心理的矛盾与不安。 台湾文坛有不少女作家,在七O年代形成女作家霸占文坛的趋势,这些台湾女作家以凸显台湾女性小说的中产阶级性格作为主要阅读策略,并以性别论述为主轴,强调这些女性作品在创作形式和性别刻画具颠覆性,企图松绑男性中心文学价值观和父权社会体制对女性的箝制。(邱贵芬) 如果九O年代的女性已不再是一群无声的族群,如果我们已有所欲求、拥有些许的权利,九O年代的女权运动就开始面对女性之间立场不一,政治目的分歧窘境。但从传统女性的角度来看,市面上有许多女性杂志仍停留在父权意识的藩篱中而不自知,而女性杂志的表现形式及编写方向(文字和女性特写为主的图片各占一半),则持续将女性物化、商品化。因此,有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女性读者在翻阅女性杂志时所得到的乐趣,是一种内化了男性观点的自虐行为,不但持续将女人视为肉欲对象,更物化、性化女人的主体,巴特契(Sandra Lee Bartky)则进一步将这种大众文化所不断鼓吹的女性身体美学称为「父权的现代化」,即在科技的推波助澜下,女人的身体已成为一门专门知识,不再为女人所控制,而只有美容健身专家及妇科医师才拥有这方面知识。女性杂志中的女性,即是符号供人观赏,也是观赏这些符号的读者;在女性杂志的阅读时空中,女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其多复位位已超过了父权社会所允许女人的唯一定位。(张淑丽)
伍、西方情色文学的发展 在提到中国情色文学的发展时,一开始就提到,古代社会对性的态度其实是坦荡自然的,西方亦然,甚至具体地表现在其「阳具崇拜」上。时至今日,在希腊、或在意大利庞贝城的古罗马废墟中,尚可看见不少古代遗留下来的巨大阳具图腾。 这种对性的坦然态度亦忠实地反映到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中。像是较平民化的喜剧、故事传说、讽刺诗文均充满着丰富的情色色彩。如古希腊喜剧大师亚力斯多芬尼(Aristophanes)之名剧《莉希斯崔塔》(Lysistrata)即是一例(赖守正,1997)。 《莉希斯崔塔》的情节如下:在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持续了二十一年之时,饱受战乱之苦的雅典妇女已经受不了丈夫与男友长期在外征战,让大家日子过的这么苦,现在竟然连原本制造提供聊以自慰的假阳具(dildos)的城市都降敌了。女主角莉希斯崔塔有感于国家被男人搞得这么糟,决定挺身而出联合敌方和我方的女性,一起来收拾烂摊子。他们的策略是要求所有女性团结起来,善用女人天生的武器来引诱男人。当自己的男人欲火焚身时,却要断然拒绝和他上床,除非他答应停止这场战争。结局是女人以自己的身体与性为武器,成功地征服了男人。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剧演出时取悦的对象清一色均是男性观众,而剧中女人赖以致胜的武器竟是女体与性。 公元八年,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的《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e)则是早期的情色文学经典之作。此书的内容公开地讨论了各种性爱姿势,以及做爱时妇女应否假装性高潮等问题。这本书完成后,奥维德被奥古斯都大帝放逐。但,真正的原因恐怕不是该书的内容,而是其它的政治因素。 事实上,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因政治因素而禁书屡见不鲜,但却不可能因某些作品内容涉及性而加以查禁。因为当时社会上对性的态度坦然而开放,根本没有所谓「淫秽」的禁忌。 到了罗马帝国灭亡,天主教独掌政教大权,对于性的坦然态度就有了改变,因为在圣经中记载,夏娃因为怂恿亚当吃下禁果,而必须为天堂的失落负责,俨然成为女性堕落的原型,并且背负着将死亡带到世界的原罪。性就像是禁果,而女人是充满诱惑且危险的,因此在教会中,告诫着男人要管好自己的女儿,否则他可能会随时投向陌生人的怀抱,而当一位妇人的丈夫不在身边时,更要小心,十字军东征时,出征的丈夫为自己的妻子锁上贞操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有一个与充满诱惑性的夏娃完全不同的典型,那就是处女般纯洁的圣母玛莉亚。她可以在完全不需要牵涉到骯脏的性的情况下完成生为女性的职责──生育下一代。在这样压抑性的标准下,能够被教会所允许的性只有是异性恋的性、以心灵为主的性、夫妻间的性和传统男上女下的性姿势(又被称为传教士姿势)。
有「现代情色文学之父」之称的意大利作家阿雷提诺( Pietro Aretino Page, 1492-1556)在十六世纪的威尼斯可说是一位以广泛大众为预设读者群的畅销作家,出身寒微的他认为生殖器是「人种河流的泉源,寻欢作乐时的神仙佳肴。......它制造了你......也产生了我。......我们应为它特别订定节庆假日以示庆祝」(赖守正,1997)。因此,在他的作品中,用字遣词都极为大胆露骨,对于性交姿势的形容描写也极为细微。其经典《对话录》(Ragionamenti,1534-36)中,当娜娜以各种隐喻的说法──如「将臼槌放到臼里」、「夜莺归巢」等──来形容性行为时,其友人安东妮亚就不耐烦的提醒她说:
情色文学如此对教会的批判及书写的大胆当然也被有关当局所查禁,最常被列举的罪状是「猥亵」或「妨碍风化」。然而其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情色文学具有批判、颠覆及踰越当时的主流价值和意识型态的功能。正因为前述的基督教文化传统,性变成了极为压抑、极为私密的,也是不能被谈论的。然而当时皇室和教廷的腐败,却不若主流规范中教育民众的。因此,情色文学的平民化也对当时的有关当局带来极大的威胁。
萨德(Sade)是性虐待文学的建立者。「虐待狂」(Sadism)这个字就从他的名字而来。由于他的作品常常呈现人性丑恶的一面,尤其是对性变态的描写,萨德对许多读者来说,可能是个罪大恶极的色情狂。然而,在他的作品中也不乏对道德的争论与哲学式的思考,因此像尼采、雨果、大仲马也是他的作品的拥护者。 萨德的情色作品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宣扬他的哲学思考,反政府的唯物论与全然性自由的乌托邦式观点。唯物论不相信人死后的世界,认为构成宇宙的所有元素都是有机体,人不过像是机器,而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享乐,这也是萨德笔下人物的写照。萨德更相信人是完全孤独存在的个体,在这样的前提下,最重要的就是每个人自己的利益。也由于个人的利益,因此无情地利用别人也是很可能的,这样才符合「自然」。因为自然的丛林法则就是告诉我们「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自然既不理性也不感性;自然也需要罪恶才能够平衡(人口控制就是一个例子)。于是,好与坏的分界已经模糊,也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因此《朱斯蒂娜》(Justine)这部小说中,虽然女主角笃信宗教、洁身自爱,但还是受到富商的追杀、神父的强暴、医生的粗言暴行,结局是女主角被雷劈死,完全不符合善恶终有报的道德观念,充分反映出萨德自然主义的色彩。 在《卧房里的哲学》中,萨德对于性偏差的描述十分仔细,将变态者、犯罪者的动机、行为、后果等刻画入微。就像他所说的,他描写的是真实存在社会中的「活的人类」。他希望这部书能成为当时研究还是新学问的性学的医师及科学家的「性偏差百科全书」。 在《索多马的一百二十天》(The 120 Days of Sodom)这部小说的引言中,萨德就说到:「没有任何事务可以限制淫欲。强化欲望的方式就是试图加以限制。」在这里萨德对于宗教的禁忌也做了批判。在他的小说中,情色也是用来从事社会批判和社会价值颠覆的主要着力点。
三、性解放vs. 阳具至上:D. H. 劳伦斯(刘亮雅,1998)
十八世纪之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颂扬女人的贞节、男人的雄风,而这恰好是其对性别概念和性道德的双重标准。女人的情欲被二分为处女或娼妓,在在训诫了中产阶级的妇女不得有性欲。而女性的性欲被界定在母职和被动迎合男性需求上,欲望的表现也受到了诸多限制。女性特质在文化建构下是看不到情欲的部分的,甚至有说法是女人是没有情欲的,即使有也是为了生育的需求。这个时期所谓「纯洁」的女性就像小孩子一样,要保护他们不受色情小说的污染与腐化。然而,佛洛依德则将女人的性欲和生育功能做了区分,他认为女人无性欲的观念是维多利亚时代对女人性欲的一种扭曲。她讨论了女性的自慰、重视性行为中的前戏、女同性恋欲,以及超出正常性行为如施虐/受虐行为。这些都说明了女性与生殖无关的性欲。然而,女性主义者批评佛洛依德仍然认为女性的性欲是被动的,他对性欲的观念是以「阳具至上」的性为中心。他认为不管在男性或女性身上,原欲必然是男性的。举例来说,他认为女性最初的性快感来自阴蒂,而阴蒂就等同于男性的阴茎。然而在成长的过程中,女性的性快感必须从阴蒂转移到阴道,而放弃「阳刚的阴蒂性感带」(erotogenic
「尔苏拉深深着迷的是她姣好、挺拔、运动员的体态,以及那不可一世的骄傲。她像男人般骄傲自由,却又像女人般细致优美……。」(引自刘亮雅,1998)
在今日的欧美学术界,乔治?巴代耶(George Bataille, 1887-1962)常被视为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当代思潮的先知。除了情色小说之外,他撰述了三本探讨情色议题的著作,在其晚年甚至称其作品可以情色一词来代表(赖守正,1995)。
玛格丽特?莒哈丝(Marguerite Duras)是法国作家。她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和六○年代的社运。她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从小说、剧本,一直到电影的导演。她关注的重点多是无助的儿童、行乞的女人、残酷的战争、不可能的爱情等,是没有国界的。她生于越南,却是贫穷的法国人,即使回到法国,都觉得自己像是个「异乡人」,这种无从归属的感觉反而让她敏锐地观察、了解到人生共通的忧虑与哀愁,同时也在书写、影像上打破了各种拘束,不论是道德、定律或理论(陈艳姜,2001)。
一、前言 女同志理论(Lesbian theory)伴随着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之发展而崛起,到了90年代卓然成家,历经不同的历史时段与种族、阶级、文化差异之冲击,而与妇女运动和同志运动相互合纵连横,以凸显性欲取向(sexuality)性别(gender)、与异性恋机制与父权结构之勾连。(张小虹,1995)
二、九0年代台湾的女同性恋小说-以邱妙津、陈雪、洪凌为例 原本荒瘠的台湾女同性恋小说园地,在90年代造成轰动,包括曹丽娟、朱天心、邱妙津、陈雪、与洪凌等人。
(一)邱妙津的抒情告白:《鳄鱼手记》与《蒙马特遗书》是爱欲、性别的书写 邱妙津是个备受争议的作家。她描写女同性恋的爱欲流动,塑造令人难以忘的T和T与婆的关系。她的小说以女同性恋为主,因而也缔造了90年代台湾女同志书写的里程碑。 《鳄鱼手记》的主角「拉子」已成为女同志的认同和代称(纪大伟,1998b)。她藉由「鳄鱼」来批判异性恋社会,也使「鳄鱼」成了某些女同志自我认同的身分(纪大伟,1998b)。然而,她的意识形态还是保守的。 拉子常表现出强烈男性认同,以启蒙者、书写者、艺术家的身分企图操控情欲、生命和文学的文本,不断地追求绝对之爱,同时拉子内化了社会歧视,自鄙自弃,以社会畸零人自居,女同性爱欲因此又成了不可能之爱。 在这样「全有或全无(all or nothing)」的纠结扭曲里,传统的性别头箍被质疑却无力甩脱,爱欲由挑逗玩虐变调为冷酷的遁逃与折磨,搁浅在痛苦无望的海涯,而拉子只以自残自虐收场。(刘亮雅,1998) 以出版的动态来观察,因自杀殒命的邱妙津名气扶摇直上,也荣登1997年同志票选梦中情人活动女性偶像榜首,在1994年与1996年,相继出版了《鳄鱼手记》及《蒙马特遗书》,这二个作品常陈列在显著位置,又是一例证。 两书都刻画沉痛惨烈的女同性恋关系,凸显女同性恋的爱欲痴狂与角力挫败,异乎一般以女同性恋仅为浪漫的精神恋爱之刻板印象。《鳄鱼手记》是台湾以同性恋为主题及题材的第一部重量级长篇小说。用第一人称叙述着拉子开宗明义地说: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我深处的「原型」的女人。 根据纪大伟对计算机网络的观察,拉子与鳄鱼均已成为女同志自我认同的名称,《鳄鱼手记》因此是台湾女同性恋次文化中的经典(纪大伟,1998)。《鳄鱼手记》承继了朱天心<浪淘沙>(1976)里校园T(butch,即扮演「男」角的女同性恋);婆(femme,即扮演「女」角的女同性恋)的罗曼史,却套进了抒情小说的形式,第一人称叙述者拉子既是T,也是书写者、艺术家,以往事追忆录的方式,回溯她与恋人的复杂关系及她的艺术家矛盾心灵,以及两者交互影响。意象、比喻和象征俯拾皆是,以精致的诗般语言描摹心境,动人心魄。拼贴式的写法穿插着T婆故事、意象式的心理描写、电影里美学意象的探索、对社会体制的议论、以及鳄鱼卡通式的诙谐讽刺剧,而形成意义极其繁复的文本。叙述时间往复于现在与过去之间,回忆是忏情与自部,也无可避免地带着某种想象的扭曲与虚构。(刘亮雅,1998) (二)陈雪的梦境小说:《恶女梦游》 就呈现女同性恋情色而言,陈雪对活动的生理细部描写大胆直接、浓烈欢畅,在台湾文坛上无人可出其右。陈雪的「恶女」也因而是带者「败德」的挑衅,而非杨照称的「罪恶」。二本小说集分别在1995年出版的《恶女书》和1996年出版的《梦游1994》里,大部分以「梦」为框架,但藉由自由联想、时间的断裂跳跃或混乱模糊、人物若有似无、及认知与记忆的不稳定性,更刻意仿真梦的机制,令人想起卡夫卡(Franz Kafka)梦魇幻境。 陈雪故事里的「梦游」是追寻潜意识里被压抑的欲望,这欲望不仅是受社会压制的女同性爱欲,更是交缠的心理郁结(例如因爱纠葛而倍受压抑的恋母与自恋情结)。在陈雪的梦游里,女同性欲望本身往往坦率炽烈,一蹴可得,反而是在潜意识更深层的纠结或对社会规训的畏惧影响了爱欲的流动与自我认同。佛洛伊德区分欲望(desire)与认同(identification),然而陈雪笔下女同性恋常混杂欲望与认同,产生相互认同、互为借镜的关系。
(三)洪凌之科幻恐怖罗曼史:《肢解异兽》与《异端吸血鬼列传》的情欲与性别 台湾女性小说家,在李昂之后,少见如洪凌这般睥睨传统、狂烈大胆之徒。洪凌的英文名字Lucifer(魔鬼)和《肢解异兽》、《异端吸血鬼列传》之书名均显露对边缘性的充分自觉及高昂的战斗力。原本在一个男尊女卑兼又反情欲的文化中,「好女人」、「好女孩」向被视为没有情欲。不但男以父权法律、宗教、道德监控女人的身体,女人更严加自我监控,甚至疏离。 90年代的台湾情欲场域已随着女性主义、同志运动所建立的论述空间而日渐开阔,但洪凌仍被视为异端中的异端,也颇具争议性。 此外,洪凌描绘男同性恋、女同性恋、S/M(sadomasochism性玩虐与受虐游戏)、阴阳人,甚至半人半兽如吸血鬼、蝎人、蜘蛛人、鱼人、狮身人面等生香活色的情欲生活。 其书写受到女情义同志运动的交相影响。她的半人半兽暗示人的动物性,而「肢解异兽」则借喻S/M极玫的爱虐快感。描写S/M蕴含的相关系,即连异性恋S/M也不例外;暗示异性恋关系中同性恋结构。其对异性恋霸权的挑衅既凌厉又充满玩谑,这样的特色亦也挪用死怖小说电影成规、刻意制造悚效果上。 另外,她对科幻、罗曼史、改写希腊神话的耽爱更带领读者走出写实小说狭窄的框框,在想象的层次中经验更多的可能性。借着混杂这些文类,洪凌营造出魔幻耸动、诡谲迷魅的气氛,将其S/M情色铺陈得泪狂绚丽,饱涨诗情的狂飙。
三、酷儿理论及其现象 所谓「酷儿」包括女男同性恋者、女男双性恋者、女男变装欲者、女男变性者以及肯定同性欲望流动之可能的女男异性恋者。 在英国1880与1890年代,「女性主义」、「同性恋」二词开始进入语汇,而「新女性唯美男性亦重新界定了阴(femininity)、阳(masculinity)之义」,引发了卫道人士的性(别)无政府(sexual anarchy)时代(2-3)。(刘亮雅,2001) 然而,在台湾的同性恋至今仍被视为异性恋主流边缘,这可以由个人出柜人数之少、而同性恋运动多以集体认同方式进行看出。且在台湾里,「同志运动」一词发展至今,多指女男同性恋(lesbian and gay)运动,但有时也指酷儿(queer)运动。 同志小说遂也包括此二涵义。其实有关同志小说的定义在西方有争议,这是因为一方面西方同志运动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给予同志的定义,在西方颇有争议,这是因为一方面方同志运动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给予同志的定义不尽相同。 纪大伟的书名挪用大岛渚的电影《感官世界》,其标出酷儿书写的主要特色。「感官」包括情色爱欲和吃喝拉撒。该书里用谐趣或怪诞的手法呈现身体官能,挑逗同性爱欲;其另一特色是大量使用后设技巧,做为颠覆体制的写作策略。 纪大伟不断搅乱情节的线,留下缺口,又顽皮地一再制造悬疑,刻意让故事变调诡奇,超乎读者期待。纪大伟是新世代杂食者,小说之外,还吸收了小剧场、艺术电影、同志动画、以及电玩角色扮演游戏(其中情节可不断改写)的手法。《感官世界》因此展现出丰富多样的实验和新的节奏感。 另一方面,同志次文化早已存在于台湾,与同志运动未必有许多交集。单性聚集的社群,像是:女校、男校、军队、监狱,甚至于社团,都提供同性爱关系或小圈子发展的机会。而像台北新公园(即现在的228纪念公园)、红楼戏院、西门町中华商场公厕,及一些咖啡馆均曾是男同志相互取暖或找性机会据点。女同志则可能较隐秘地选择以咖啡馆家庭聚会方式社交。至80与90年代女男同志则都渐以同性恋酒吧、学校1社团等为社交场所。 当然,小说家未必是运动者,也未必关心本土运动的发展,他/她书写同志题材可能出于自身经验与观察,也可能受到欧美同志/酷儿运动、小说、电影、与MTV及中文小说等的影响。如中国的曹雪芹《红楼梦》与陈森《品花宝鉴》中对同性爱欲的描写颇受瞩目;而欧美作家如普鲁斯特、汤玛斯曼、纪德、佛斯特的同志小说也早已为人所知。而80年代末期,或因国外同志/酷儿运动的热潮,以及解严之故,媒体已大量介绍同性恋。
李安的《喜宴》与蔡明亮的《河流》分别于1994年和1996年获国际影展大奖,朱天文《荒人手记》和邱妙津《鳄鱼手记》分别于1994与1995年获时报百万小说奖,都有助于同志艺术在台湾的建制化(establishment)。这些或可以说明何以台湾同志/酷儿运动是个极其小众的运动,然而解严以来书写同志题材的作家却不下五十个,面对父权社会对性别情欲深固的禁忌,书写本身即是心灵解严的开始。
赖守正。<情色/色情文学/政治>。《第六届英美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书林出版社,1997a。 赖守正。<禁忌与踰越──巴代耶的情色观>。《性别研究的新视野──第一届四性研讨会论文集(下)》。台北:元尊文化,1997b。 赖守正。<情色文学与翻译>。《中外文学》。2000年10月。 陈艳姜。<欲望之流:莒哈丝的「中国情人」与书写越界>。《中外文学》。第30卷,第4期。2001年9月。 宋美王华。<劳伦斯之异色:性爱/道德/诠释>。《联合文学》。第70期。1980年8月。 黄暄。<莺莺传之性别解读(毒?!):女性身体、欲望与价值秩序>。《妇女与两性研究通讯》。第55期。2000年6月。 孙琴安。《中国性文学史》。台北:桂冠,1995年。 叶庆炳。《中国文学史》。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台北:桂冠,1991年。 福田和彦。《中国春宫画》 <郊特牲>。《礼记》。《礼记注疏》卷二六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达史》。台北:中华书局,1962年。 金赛着,文风编译社译。《女性性行为》。台南:经纬书局,1954年。 翟本瑞。<比较哲学的不可比较性:以情欲开展为例>。《思想与文化的考掘》。嘉义:南华大学出版,1999年。 翟本瑞。<中国人性观初探>。《社会理论与比较文化》。台北:洪叶文化,1999年。 张小虹。《后现代/女人:权力、欲望与性别表演》。台北:时报,1991年。 张小虹。《性别越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台北:联合文学,1995年。 张小虹。《欲望新地图》。台北:联合文学,1996年。 张小虹编。《性/别研究读本》。台北:麦田,1998年a。 张小虹。《性帝国主义》。台北:联合文学,1998年b。 丁乃非。<秋千.脚带.红睡鞋>。《性/别研究读本》。台北:麦田,1998年 张淑丽。<解构与建构之后-女性杂志、女性主义与大众文化研究>。《性/别研究读本》。 台北:麦田,1998年 邱贵芬。<族国建构与当代台湾女性小说的认同政治>。《性/别研究读本》。台北:麦田,1998年。 佛洛依德,林克明译。《性学三论 爱情心理学》。台北:志文,1971年。 劳伦斯,叶颂姿译。<性与可爱>。《劳伦斯散文选》。台北:志文。1986年。 刘亮雅。《欲望更衣室:情色小说的政治与美学》。台北:元尊文化,1998年。 刘亮雅。《情色世纪末:小说、性别、文化、美学》,台北:九歌,2001年。 梅家玲。《性别论述与台湾小说》,台北:麦田,2000年。 周华山。《同志论》。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年。 纪大伟。《感官世界》。台北:平氏,1995。 纪大伟。《膜》。台北:联经,1996年。 纪大伟。《酷儿启示录:台湾当代Queer论述读本》。台北:元尊文化,1997年。 纪大伟。《恋物癖》。台北:时报,1998年a。 纪大伟。《晚安巴比伦:网络世代的性欲、异议与政治阅读》。台北:探索,1998年b 许佑生。《男婚男嫁》。台北:开心阳光,1996年。 张娟芬。《同女出走》。台北:女书,1997年。 张娟芬。《姊妹「戏」墙》。台北:联合文学,1998年。 邱妙津。《寂寞的群众》。台北:联经,1995年。 邱妙津。《蒙马特遗书》。台北:联经,1996年。 邱妙津。《鳄鱼手记》。台北:时报,1997年。 陈雪。《恶女书》。台北:平氏,1995年。 陈雪。《恶魔的女儿》。台北:联合文学,1999年。 洪凌。《肢解异兽》。台北:远流,1995年。 何春蕤。《性心情:治疗与解放的新性学报告》。台北:张老师,1996年。 何春蕤。《从酷儿空间到教育空间》。台北:城邦,2000年。 八王子。《八王子遗书》。台北:唐山,2000年。 Diane Wood Middlebrook著,朱恩伶译 《男装扮终生: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性别演员──爵士乐手比利.提顿的双重人生》。台北:女书,2001年。 李美枝。《性别角色面面观》。台北:联经,1987年。 王行。《解放男人:男性的自觉与成长》。台北:探索,1998年。 吴若权。《谁能让男人付出真心》。台北:方智,1998年。 蔡诗萍。《你给我天堂,也给我地狱》。台北:联合文学,2000年。 酷儿Queer。《岛屿边缘》。台北:唐山,1994年。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编。《第三届「性/别政治」超溥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坜:中央大学,1999年。 Lai, S. C. (1998)”Power/Pleasure/Danger: The Context and Conflict of Feminist Appropriation of the Erotic”.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24, 191-211.
|
|||||
| 文章录入:okuc 责任编辑:okuc | |||||
|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
| 最新热点 | 最新推荐 | 相关文章 |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管理登录 | | |
 |
粤ICP备05083455号 Copyright 2004-2005 CulChina.Net 主办:深圳大学文学院·传媒与文化研究中心 站长:孙海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