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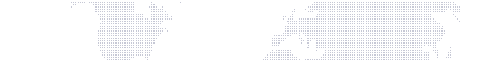
| | 网站首页 | 文章中心 | 学术动态 | 资料下载 | 建议留言 | 文化论坛 | 学人博客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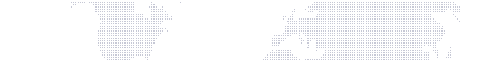 |
| 您现在的位置: 文化中国 >> 文章中心 >> 文化前沿 >> 文化理论 >> 文章正文 |
|
|||||
| 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论哈贝马斯的规则观 | |||||
| 作者:童世峻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12-13 | |||||
|
提要: 哈贝马斯的规则观涉及三个问题:遵守规则的条件、规则意识的产生和规则正当性的辩护。他把主体间性看作是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关键:离开了主体间性,就无法知道某人是不是在遵守一条规则;离开了主体间性,就既不能形成“规则意识”,也不能从“规则意识”中发展出“原则意识”、分化出“价值意识”。离开了主体间性,更无法为规则的正当性提供辩护。哈贝马斯之所以关注规则概念,是因为他关注这样三个问题:“区别于自然现象的社会现象的研究何以可能?”、“现代社会中真正自由的人格何以可能?”、“现代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辩护何以可能?”。为了回答这三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哈贝马斯用他的交往理性概念来扬弃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把康德关于“无规则即是无理性”的观点和哈贝马斯的“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的观点综合起来,可以得出“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理性”的结论。
康德(Imanuel Kant)说:“无规则即是无理性”。1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则强调,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讨论哈贝马斯的规则观,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规则这个社会现象本身,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主体间性”概念的意义-理解它包含什么内容、它为什么是重要的。进而,如果我们把康德的观点与哈贝马斯的观点结合起来的话,我们还可以对“理性”和“主体间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有更好的理解。
在哈贝马斯做出的诸多概念区分中,“行动”(德语的Handeln和英语的action)和“行为” (德语的Verhalten和英语的behavior)的区别是最基本的一个。国内出版的哈贝马斯著作的中文译本有不少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译成“交往行为”。这样的译法当然也有它的道理。一方面,“行为”的含义宽于“行动”、因而也包括“行动”。另一方面,在现代汉语中,“行为”似乎显得比“行动”更抽象一些、更像一个理论术语一些。但是,不管在翻译其它著作时是不是可以把德语的Handeln和英语的action译成“行为”,在哈贝马斯那里这肯定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哈贝马斯非常强调Handeln与Verhalten的区别,也就是action与behavior的区别。人们一般用“行为”一词来翻译Verhalten和behavior。如果也用这个词翻译Handeln和action,会出现两种可能:或者是不得不取消Handeln(action)与Verhalten(behavior)的区别,或者是不得不用“行为”以外的一个词来翻译Verhalten(behavior)。3 前一种情况是对哈贝马斯的严重误读,后一种情况则无法体现Verhalten这个词、尤其是behavior这个词与Behaviorismus/behaviorism(行为主义)这个词的词源上和意义上的密切联系。 在哈贝马斯看来,“行动”和“行为”之间的关键性区别,在于前者一定是意向性的,而后者可以是非意向性的-事实上他常常用这个词表示非意向性的行为。41971年哈贝马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了一系列演讲,其中第一个演讲的第一节的标题就是“行为与行动的区别”(Verhalten versus Handeln/Behavior versus action)。简单地说,行动区别于行为之处在于行动是意向性的,行为则不是意向性的;而行动之所以是意向性的,是因为行动是受规则支配的。哈贝马斯写道: “行为如果是由规范支配的、或者说是取向于规则的话,我就把它称为意向性的。规则或规范不像事件那样发生,而是根据一种主体间承认的意义[Bedeutung]而有效的。规范具有这样一种语义内容,也就是意义[Sinn],一旦进行意义理解的主体遵守了这些规范,它就成为他的行为的理由或动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论的是行动。其行动取向于规则的行动者的意向,与该规则的这种意义相符合。只有这种取向于规则的行为,我们才称为行动;只有行动我们才称作意向性的。”5 这里,哈贝马斯把行动的“意向性”和行动的“遵守规则性”联系起来,但没有对两者之间的联系做出具体说明。在其它一些著作中,尤其是在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动理论》中,哈贝马斯借助于维特根斯坦有关“遵守规则”的论述对这种联系进行了说明。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联系的关键在于行为的意向性取决于“意义的同一性”,而意义的同一性则依赖于规则的主体间有效性。行为作为一种意向表达所具有的意义是无法仅仅依靠客观的观察来把握的,因为从观察者的视角出发,我们只能看到符号的“意义的持续性”(Konstanz der Bedeutungen),即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了同样意义的行为;但这种意义的持续性不等于“意义的同一性”(Identitaet der Bedeutungen):重要的不是仅仅知道在哪些情况下出现了哪些同样的行为,而是知道哪些行动被当作是同样的行为-也就是具有相同意义的行为。“对同样符号的具有持续意义的使用,决不仅仅是现成地给与的,而是要能够为符号使用者自己所知道的。而能确保意义的这种同一性的,只能是‘约定地’确定一符号之意义的一条规则的有效性[Geltung]。”6 说得具体些:当我们从客观的观察者的角度谈论某种特定类型的意向性行为或具有某个特定意义的行动的出现频率的时候,我们已经假定了我们已经理解了这种行动的意义是什么,而这种意义不能仅仅是客观观察者所强加的,而也应该是为行动者自己所理解的。但问题是,某种类型的行动总是发生于不同的具体情境的,我们有什么依据来确定在这些不同情境中发生的行为是具有相同意义的行动呢?哈贝马斯强调,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固然不能仅仅依据客观的观察,但也不能仅仅依据行动者自己的理解;因为,否则的话,一个人以为自己在实施同样的行动,就会等同于他实际上是在实施同样的行动了。在这里,哈贝马斯引用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的一条著名论证,即关于人们不可能独自地遵守规则的论证:“一个人以为在遵守一条规则,并不就是在遵守一条规则。因此,规则是不可能‘私下地’遵守的:否则的话,以为自己在遵守一条规则,就会与遵守规则是同一回事了。”7 对此哈贝马斯解释说: “这个考虑的要点,是说如果不存在甲的行为可以受到乙的批判-一种原则上有可能达成共识的批判-的情况的话,甲是无法确信他到底是不是在遵守一条规则的。维特根斯坦想要表明的是,规则的同一性和规则的有效性是从头到尾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遵守一条规则,意味着在每一个场合遵守同一条规则。规则在其多样的实现之中的同一性,并不依赖于可观察的不变性,而依赖于它的有效性的主体间性。规则之成立是虚拟的,所以就有可能对规则支配的行为进行批评,并评价它是成功的还是不正确的。这样,对于甲和乙来说,就预设了两种不同的角色。甲具有遵守规则的能力,因为他避免系统的错误。而乙则具有判断甲的规则支配行为的能力。乙的判断能力又进一步预设了规则能力,因为乙要能够进行所要求的检验的话,他就必须能够向甲指出他的错误,并且,如果必要的话,形成一种有关该规则之正确运用的一致意见。这样,乙就接过了甲的角色,向他表明他做错在哪儿。在这种情况下甲接过了裁判者角色,并进一步又可能通过向乙显示用错规则的是他[乙]而对自己起初的行为加以辩护。没有这种相互批评和导致一致意见的相互指教的可能性,规则的同一性是不可能确保的。一个主体如果要能够遵守一条规则-也就是说,遵守同一条规则-的话,这条规则就必须对于至少两个主体而言主体间地具有有效性。”8 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之所以在“以为自己在遵守一条规则”和“确实在遵守一条规则”之间做出区别,是因为对一个主体(甲)来说,如果他的行为无法受到另一个主体(乙)的批评的话,他是无法确切地知道他是不是在遵守一条规则的。规则的同一性取决于规则的主体间的有效性,而规则的主体间的有效性,是指只有通过一个主体(甲)在另一个主体(乙)的批评面前成功地捍卫了说自己是遵守了一条规则的立场之后,才能说他不仅仅是认为他在遵守规则,而确实也有理由说他在遵守规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存在着一条适用于甲和乙的行为的规则。 哈贝马斯在进行上述分析的时候,克里普克(Saul Kripke)的《维特根斯坦论规则和私人语言》(1982)一书还没有发表。哈贝马斯在此后发表的著作中,也没有提到克里普克这本书的观点。但哈贝马斯对维特根斯坦的规则论的理解,与克里普克在该书中所作的引起广泛注意的诠释,是有相当接近之处的。克里普克在该书中的一些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上面讨论的哈贝马斯的观点。 克里普克说,一般认为是《哲学研究》第243节才开始的那个著名的反对私人语言的论证,其实在这以前就开始了,甚至它的结论在第202节就已经做出了。这202节,就是前面提到的哈贝马斯引用的那段话。在克里普克看来,维特根斯坦的这段话,是对前一节即第201节中提出的一个悖论的回答:“这就是我们的悖论:没有一种行动是可以被一条规则所确定的,因为每种行动都可以根据那条规则做出来。”9克里普克认为这个问题是整个《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其实质是一种新形式的怀疑论,甚至是“哲学迄今为止所曾见过的最彻底最独创的怀疑论。”10在克里普克看来,维特根斯坦的真正问题并不是:“我们怎么能够表明私人语言-或某种其它特殊形式的语言-是不可能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表明任何语言(公共的、私人的或不管什么语言)是可能的?”11 克里普克把维特根斯坦的问题与休谟(David Hume)的问题作比较。休谟认为,只有当具体事件a和b被认为是分别属于两个事件类A和B-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A类的所有事件后继着B类的事件”这样一个概述建立起来的-的时候,我们才能说a是b的原因。当仅仅考虑a和b本身的时候,并没有可运用的因果关系。克里普克认为休谟的这种论证可以叫做“私人的因果性的不可能性”论证。维特根斯坦关于私人语言的不可能性的论证,就像休谟的私人因果性的不可能性论证一样,是他对怀疑论问题的“怀疑论解决”。对一个怀疑论问题可以有两种形式的解决。一种是直接的解决,即表明经过更仔细的考察,怀疑论被证明是不可靠的;一个更深奥复杂的论证,被用来对怀疑论者所怀疑的那个命题提供证明。笛卡尔对自己的哲学怀疑所提出的就是这样一个直接的解决。与此相反,对怀疑论问题的怀疑论解决,是先承认怀疑论者的否定性论断是不可回答的,然后表明,我们的日常的实践方式(practice)或信念之所以为正当的,是因为它其实并不需要怀疑论者表明为不可得到的那种辩护。怀疑论论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表明了这样一点:一个日常的实践方式,如果要对它进行辩护的话,这种辩护是不可能以某种方式进行的。维特根斯坦的“怀疑论解决”的要点是:它不允许我们谈论被作为孤立个人本身考虑的说话者有任何意谓。 在解释维特根斯坦的这个怀疑论解决的时候,克里普克认为维特根斯坦像休谟一样,实施了所谓“条件句的转换”,通过这种转换把原先的问题给消解掉了。对于常识来说,有这样一个条件句:如果类型A的事件是类型B的事件的原因,那么,如果类型A中的一个事件e发生了,那么类型B的一个事件e'就必定随之而来。休谟对这个条件句进行了换位,从而颠转了我们所强调的重点:不再把因果联系看作是首要的,以为观察到的规则性(regularities)是由此而来的;相反,休谟派把规则性看作是首要的,并且指出在相应的规则有一个反例的时候,我们就取消一个因果假说。与此相仿地,维特根斯坦也对以下条件句进行了换位:“如果约翰把‘+’理解为相加,那么,如果要他回答‘68+57’,他就会回答‘125’。”换位的结果是:“如果约翰在被要求回答‘68+57’的时候没有回答‘125’,我们就不能说他把‘+’理解为相加。”(当然这里省略了一些复杂情况)。这样,约翰把“+”理解为相加这一点并没有独立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能对他是不是有了理解、有没有一种特定的精神状态做单独的考察。重要的是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就约翰是不是把‘+’理解为相加而达成一致意见。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对他的问题的怀疑论解决,取决于一致意见,取决于可检验性-取决于一个人检验另一个人是不是像他那样有能力使用一个词项。”12问规则能不能被私人地遵守的问题,并不是问一个像荒岛上鲁宾孙那样的人能不能遵守规则。克里普克说: “...如果我们要认为鲁宾孙是在遵守规则的,我们是把他放到我们的共同体中加以考虑,并且把我们关于遵守规则的标准运用于他。说那个私人[语言]模型是错误的,其意思不必是说一个物理上孤立的个人是不能被说成是遵守规则的;它的意思毋宁是:一个个人,如果孤立地考虑的话(不管他是否在物理上是孤立的),是无法被说成是遵守规则的。”13
第一,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只有当行动者甲和乙能够彼此对对方是否遵守着一条规则做出判断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遵守这条规则。当我们追随维特根斯坦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已经假定了甲和乙是具有规则意识的和遵守规则的能力的-成问题的是他们能否知道遵守一条特定规则意味着什么,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遵守规则意味着什么。一般意义上的遵守规则意味着什么,是一个有关规则意识或遵守规则的能力之形成的问题的重要方面。对这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回答。 第二,规则意识不仅仅是一个对规则之内容的了解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懂得“遵守规则”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而是把规则当作自己行动的理由和动机的问题。主体如何能够形成一种把规则当作行动理由和动机的意识或能力,这个问题维特根斯坦也没有回答。 上述两个方面同属于甲和乙“双方的规则意识的产生”这个“发生学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哈贝马斯借助于对米德(Herbert Mead)的社会行为主义的分析来加以回答。14 哈贝马斯认为,在二十世纪初,意识哲学的主客观模式在两个方面受到攻击:分析的语言哲学和心理学的行为理论。两者都怀疑通过直觉、反省来研究意识现象,但采取不同的方法,一个是从主体意识转向主体间的语言活动,一个是从主体意识转向可观察的身体行为。哈贝马斯认为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虽然直接属于后一个传统,但他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反对,尤其是他对于主体间交往的重视,使他突破了这个传统,从而能够与另一个传统-语言哲学-进行卓有成效的相互诠释。哈贝马斯对维特根斯坦有关“遵守规则”观点的讨论,就是当他在维特根斯坦和米德之间进行的相互诠释的一例。 哈贝马斯所说的“规则意识”或“规则能力”,米德称为在“主我”(I)之中的“宾我”(me),而这种“宾我”,实际上是我这个主体在与其他主体发生互动的过程中,把他们对我的期望内在化的结果。主体或自我(ego)可以在两种意义上发生主我(I)和宾我(me)的关系。一种情况是在记忆中:“我与自己讲话,我记得我先前所说的话,或许还有与之伴随的情感内容。这一时刻的‘主我’(I)出现在下一时刻的宾我(me)之中。”15 在这里,主我仅仅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出现的;我在意识中能够把握到的仅仅是过去的我。但主体还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发生主我和宾我的关系,而这两者同时构成了自我的不可缺少的环节:米德把“宾我”称为“一个人自己采取的诸多他人的态度的系统组合”,而把“主我”称为有机体对他人的态度的反应。规则意识的形成,可以理解为米德所说的这种“宾我”的形成过程。 哈贝马斯在规则观方面对米德观点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主体的语言规则的意识的产生。假定一个部落成员甲对部落的其他成员(如乙、丙、丁)呼叫:“有袭击!”现在的问题是:甲如果要获得一种规则意识、因而有可能根据一条规则来产生一个呼叫"q",他应该采纳乙的态度具有什么性质。假如甲发出q以后,乙、丙、丁却没有来救他。假如没有客观的情况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没有来,那就不存在救援未能出现的问题,而是乙、丙、丁等拒绝来救援的问题。乙、丙、丁使甲的期待失望了,表明一种交往的失败,而对这种失败,甲是负有责任的。那些听到呼叫的人对这种失败用拒绝救援的方式来做出不予理会的反应。现在,决定性的步骤是甲要把乙、丙、丁的这种不理会的反应当作对q0的运用不当而内在化,。“如果S-当他‘语义上’出现差错的时候-学会对自己采纳乙、丙、丁等对他采纳的那种否定的立场,并且如果乙、丙、丁等人自己也用相同方式来对待类似的失望,那么,这个部落的成员就学会这样来彼此发出呼叫,使得他们在q0发得不适当的情况下,会预期得到批判性的反应。在这种期待的基础上,一种新型的期待就会发生,也就是这样一些行为期待(c),它们的基础是这样一个约定:一种声音姿态只有当它是在特定情境条件下发出时,才会被理解为‘q’。这样,我们就达到了经由符合中介的互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符号的运用是由意义约定所确定的。对互动的参与产生出受规则指导的符号表达,也就是说,伴随着这样的默会期待:它们会被别人承认为是符合一条规则的表达。”16 哈贝马斯说,如果对米德的命题作上述阐述,它“就可以被理解为对维特根斯坦的规则概念-首先是支配符号使用的规则,对意义做约定的确定、因而确保意义的同一性的规则的概念-所做的发生学说明。”17 第二个层次,是主体的行动规则的意识的产生。行动规则不等于语言规则。语言规则的基础是约定,而行动规则的基础不仅仅是约定。对这一点我们下一节再讨论。这里要指出的是行动规则和语言规则的这样一个区别:不同主体遵守同样的行动规则的结果是这些主体的行动之间的协调,而不同主体遵守同样的语言规则的结果是他们之间进行成功的交往。米德对主体之间的语言交往没有给与充分的关注,就匆匆过渡到对不同主体之间行动的协调的问题,哈贝马斯对此表示不满,因为他认为只有对语言交往的各种向度(分别对应于真实、正当和真诚等“有效性主张”)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才会对行动规则的协调行动作用出合理的解释。尽管如此,哈贝马斯对米德通过对不同主体之间行动协调问题的研究所提出的“通过社会化的个体化”的思想,给与高度评价。 哈贝马斯把米德看作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个体化(individuation)问题的回答。对这个问题,西方哲学家的探索已经有了长久的历史。与把空间和时间当作个体化原则的经验主义传统相比,哈贝马斯认为那种从质的规定出发来表示个体性的哲学努力更值得重视。在这方面成就最高的是费希特,他不仅把个体性与主体性相联系,而且把主体的个体性看作是通过自我(ego)与他我(alter ego)之间的主体间关系而产生的。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费希特用主体哲学的概念只能把个体性定义为对自己的限制,定义为对实现自己的自由的放弃-而不是定义为对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创造性培育。主体只能是彼此的对象,因而即使在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限制的影响中,它们的个体性也并不超越对策略性选择自由-其典型是私人自主的法律主体的任意意志-的客观主义规定。”18 一旦对主体自由的限制被当作法律的东西而引出来,即使是法律主体的个体性也丧失了它的全部意义,因为,在费希特那里,法律代表的是“普遍自我”。 哈贝马斯认为费希特尽管没有解决、但确实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个体性和语言主体间性的关系问题,二是个体性和生活史认同的关系问题。洪堡(W. von Humboldt)和克尔凯郭尔(S. Kierkegaard)从一个已经经过历史思维模式改造的视角出发分别着重讨论这两个问题,而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则把这两条线索统一在一起,其办法是表明以下这一点:他人或其他主体对于自我的要求或期望,对于在宾我当中唤醒主我的自发活动的意识-也就是形成独一无二的自由而负责的个体-是必不可少的。米德要解开的是这样一个循环:主格的我要能够揭示自己,就必须把自己变成宾格的我。米德不是在意识哲学的框架内把这个宾格的我归结为意识的对象,而是过渡到以符号为媒介的互动的范式,真正把它当作另一个自我。哈贝马斯写道: “一旦主体性被设想为一个人自己的表象的内在空间,一个当表象客体的主体折返-就像在一面镜子中那样-到它的表象活动上来的时候所揭示出来的空间,任何主观的东西就都将只能以自我观察或反思之对象的形式而被接近-而主体本身则只能被当作一个在这种凝视之下被‘客观化’的‘宾我’。但是,这个‘宾我’一旦抛开这种具有物化作用的凝视,一旦主体不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说话者的身份出现,并且从一个听话者的社会视角出发与他在对话中面对,它就学会把自己看成、理解成另一个自我的他我(alter ego)..."。19 哈贝马斯强调必须把认识主体的认知性自我关系(self-relation/ Selbstbeziehung)和行动主体的实践性自我关联(relation-to-self/ Selbstverhaeltinis)区分开来。米德未能明确区分这两种关系,因为他把认识看作是解题,把认知性自我关系看作是行动的功能(函数)。但是,哈贝马斯说,一旦实践性自我关联的动机向度发挥作用,"主我"和"宾我"这对核心的概念对子的意义就悄悄地改变了。原先统一于本能性反应模式中的行动反应和认知反应这两个方面,现在分化开来了。符号媒介互动阶段上的自我行动控制,现在上升到不同主体之间的行为协调;生物体的共同的本能和彼此适应的行为方式,现在代之以“规范地一般化了的行为期待”。这些规范必须通过或多或少被内在化了的社会控制而扎根于进行行动的主体之中。由此而达到的社会建制与人格系统中行为控制之间的这种对应,米德也借助于采纳一个他者-这个他者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中对自我采纳一种施为性态度-的视角这个熟悉的机制来解释。但是,哈贝马斯强调“采纳他者视角”与“采纳他人角色”之间的区别,后者意味着自我采纳了他者的规范性期待而不仅仅是认知性期待。与这些期待的规范性质相对应的是这第二个“宾我"的改变了的结构,以及自我关系的不同功能:“实践性自我关联的这个‘宾我’不再是一个原初性的或被反思的自我意识的所在,而是一种自我控制的力量。自我反思在这里履行的是动员行动动机的特殊任务,是内部控制一个人自己的行为模式的任务。”20 哈贝马斯结合科尔贝格(L. Kohlberg)的道德心理学和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对米德有关自我的个体化与自我的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观点进一步做了不少阐述和发挥。从哈贝马斯表明的这三个理论之间的“反思平衡”中,我们可以对主体间性和规则意识形成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了解。 科尔贝格的道德心理学研究的重点是个体的道德意识的发展过程。在他看来,在实质内容上互相区别的那些道德判断的表层下面,存在着这样一些普遍形式,它们可以被排序为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之发展的不同阶段:前俗成的(pre-conventional) 、俗成的(conventional)和后俗成的(post-conventional)。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三个阶段上道德意识的特点,可以用相应的主体间互动类型和主体间期待类型加以解释。对应于前俗成阶段的,是关于特定行动及其结果的具体的行为期待;对应于俗成阶段的,是彼此相互联系的一般化了的行为期待,亦即规导行动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规范。本文所说的“规则意识”,首先就是这样一种理解为社会角色和社会规范的行为期待。在这个阶段上,主体不再仅仅把某个权威(家长、老师)的特定命令和与之伴随的奖赏惩罚当作其行动的指导,而学会了一些一般规则。根据米德的“通过社会化而个体化”的命题,这个过程同时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自主活动能力的提高(也就是个体化程度的提高),二是主体对于体现在(涂尔干尤其重视的)社会分工的各个角色中的规则的学习(也就是社会化程度的提高)。 但哈贝马斯注意到,米德并没有把这种意义上的规则意识或“宾我”与主我等同起来,也就是说,米德实际上看到了仅仅在这个阶段,自我还没有完全取得它的个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米德之所以没有把这种“宾我”与“主我”等同,是因为这种“宾我”所承担的道德意识,还只是一种坚持一特定群体之常规和惯例的道德意识:“它代表的是一个特定的集体意志高于一个还没有取得自主形态的个体意志的力量。”21在这个阶段,自我之有可能进行有责任的行动,是以盲目服从外在社会控制作为代价的。超越这个阶段的是科尔贝克的所谓“后俗成”阶段的自我认同。形成这种后俗成的自我认同的关键,是随着社会分化的压力和各种相互冲突的角色期待的多样化,包含在“宾我”之中两个向度彼此分化开来。一个是道德向度,它使得主体能够用普遍的道德原则来评价哪些常常相互矛盾的特定规则;一个是伦理向度,它使得主体能够根据他认为对于他这个个体是“好”的价值来筹划唯有他自己才能加以筹划的他的生活。关于前者,我们可以说是从“规则意识”向“原则意识”的发展;关于后者,我们可以说是从“规则意识”分化出“价值意识”。当然,哈贝马斯本人并没有使用“原则意识”、“价值意识”这样的说法。 规则(或规范)、价值和原则都具有规范力(normative force),也就是说对于人们的行动和选择有指导作用,但它们所起的指导作用的方式、它们本身之受到辩护的方式,都是不同的。关于规范和原则之间的区别,哈贝马斯认为如果可以把规范看作是“普遍化了的行为期待”的话,那么也可以把原则看作是“较高层次的规则”或“规范的规范”。在道德意识的“俗成阶段”,行为是根据对于规范的取向和对规范的有意的违反来判断的;在道德意识的“后俗成阶段”,这些“规范本身也要根据原则来加以判断”。22 从逻辑上说,“规则总是带着一个‘如果’从句,明确说明构成其运用条件的那些典型的情境特征,而原则,要么其出现时带着未加明确说明的有效性主张,要么其运用仅仅受一些有待诠释的一般条件的限制。”23 关于规范(尤其是用来辩护规范的原则)与价值的区别,哈贝马斯做过这样一个概括:“规范和价值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所指向的行动一个是义务性的,一个是目的性的;其次在于它们的有效性主张的编码一个是二元的,一个是逐级的;第三在于它们的约束力一个是绝对的,一个是相对的;第四在于它们各自内部的连贯性所必须满足的标准是各不相同的。”24 这里我们不对这些区别作进一步解释,而只想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从“规则意识”发展出来的“原则意识”和与“规则意识”分化开来的“价值意识”,在哈贝马斯看来是用来回答两类不同问题的。一类是“道德问题”或“正义问题”,它们原则上可以依据正义的标准或利益的可普遍化而加以合理的决定;一类是“评价问题”或“伦理的问题”,它们属于有关“好的生活”的问题这个大类,并且只有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生活形式之中或在一个个体的生活形式之中才可能进行合理的讨论。道德问题的形式是:“什么是对所有人同等地好的?”伦理问题(就一个特定个人而不是一个特定团体而言)的形式是:“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哈贝马斯曾经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两类问题之间的区别:“有人在急需时会愿意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地欺骗不管其名称是什么的哪家保险公司-我是否想要成为这样一个人,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只涉及我的自尊,或许也涉及他人对我的尊重,而不涉及我对所有人的同等尊重,因而也不涉及每个人都应该给与所有其它人的人格完整的对等尊重。”25 第二,在“后俗成”的阶段上,无论是“原则意识”的形成,还是“价值意识”的形成,都是与主体间交往密切相连的。随着对社会所强加的僵化的约定的抛弃,个人一方面必须承担起做出他自己的涉及他人利益的道德决定的责任,另一方面必须靠自己来形成一种产生于他自己的伦理自我理解的个人生活方案。哈贝马斯强调,要做出这两方面独立成就的个人,仍然完全是由社会所构成的:“通过摆脱特定生活情境而完全跳出社会之外、而落脚于一个抽象的孤立和自由的空间,是不可能的。相反,要求这个个人做出的那种抽象,就处于文明过程已经指向的那个方向之中。”26 这个方向,就是社会的现代化的过程,是人们之间的交往范围越来来扩大的过程。这个范围,从时间上说包括我们的后代;从空间上说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团体之外的他人。归根结底,文明发展的方向指向的是一个无限制的普遍商谈论域。具有“后俗成”阶段道德意识的人们,不论是做基于原则的道德判断,还是做基于价值的伦理决定,都在独自承担起做出这种判断和决定的责任的同时,诉诸一个交往共同体(道德的交往共同体原则上包括全人类,而伦理的交往共同体则只包括分享某些价值的人们),作为要求承认其为有能力做出独立判断和决定的个体、承认其判断和决定之为合理的“上诉法庭”。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道德判断的形成(就像伦理自我理解的达到一样)被引向这样一个理性论坛,它同时把实践理性加以社会化和时间化。卢梭的‘普遍化公众’和康德的‘本体世界’,在米德那里具有了社会方面的具体形式和时间方面的动态性质;这样一来,对一种理想化交往形式的预期,应该是保存了意志形成的商谈程序的一个无条件性环节的。”27 换句话说,后俗成自我认同的形成仍然是从自我出发经过他我回到自我,但是,最后回到的这个我-“宾我”,已经不仅仅是作为其他他我的他我,而是作为每个共同体中所有他者的他我。这个“宾我”之所以可能,现在不是通过一个“先在”的互动关系,而是作为“主我”之“投射”的那个理想化互动情境的结果,只有依靠这个互动情境,才有可能在高一层次上对崩溃了的俗成阶段自我认同加以重构。哈贝马斯一方面强调这种重新构成的自我认同即后俗成自我认同必须被设想为一种由社会而构成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承认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一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的乌托邦性质:“一种后俗成的自我认同只能将自己落脚在对于非强制的相互承认的对称关系的预期之中。”28 但这种“预期”又不仅仅具有乌托邦性质。为了说明这种预期的特点,哈贝马斯借用了分析哲学的规则论所做的一个经典区分-“范导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的区分。29 哈贝马斯说他不愿意把交往共同体当作康德式的“范导性理念”,因为对于“不可避免的理想化语用预设”来说,范导性和构成性之间的非此即彼是不适用的。这些预设无论在何处都没有充分实现,因为现实的交往行动过程或多或少是受到强制和扭曲的。就此而言,这些预设确实是范导性的。但重要的是,离开了这些预设,交往行动就不再可能-就此而言,这些预设又是具有构成性意义的。30
说规则的正当性问题与主体间性问题有关,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哈贝马斯指出规则有不同类型,它们的正当性问题与主体间性的联系因此也有不同的情况。哈贝马斯把规则区分为三类,这三类分别是对于三种类型的有关“应当”的问题的回答。除了前面提到的“道德问题”和“伦理问题”之外,还有所谓“实用的问题”。与此相应的有道德规则(原则)、伦理规则(准则)和技术(策略)规则。 哈贝马斯的这些思想直接来源于康德。康德把“命令式”分成三种:技术的、实用的、道德的。31技术规则实际上是关于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为了实现给定的目的,要使用什么样的手段。这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的基础是一种结果和原因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非常确定的,所以康德说表述技术规则的命题是“分析的”。在技术规则那里,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有各种各样,而在实用的规则那里,要实现的目的就是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用的规则像技术的规则一样也是一种关于目的和手段关系的规则。但区别在于,幸福常常是因人而异的:甲认为是幸福的东西乙未必认为是幸福,因而幸福和达到幸福的手段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这与技术规则不一样。但技术规则和实用规则都是有条件的规则-如果你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你就应当怎么行动,在这点上它们都区别于道德规则。道德规则是无条件的规则;它所规定的是作为有限理性主体的人无条件地应当做的事情。这就是康德著名的“绝对命令”。哈贝马斯所讲的“实用的问题”,相当于康德的技术规则所涉及的问题。哈贝马斯所讲的“伦理的问题”,虽不能与康德的实用规则完全对应,但也是关于人们对“幸福”或者“好”的生活的理解的。哈贝马斯的“道德的问题”,则基本上对应于康德的绝对命令所回答的问题。32 在着区别;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伦理规则的有效性基础是一个特定的伦理共同体的主体间承认,而道德规则的有效性基础则是一个原则上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的主体间承认。在个体道德意识的“后俗成”阶段,以及与之对应的社会建制发展的“后传统”阶段,这种主体间承认都不仅仅是主体之间的准事实的“约定”,而是主体之间的基于理由的“共识”。共识和约定一样都是可以由人改变的,但共识比约定多了理由的限制-只有当新的理由出现的时候、只有当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在所提交的理由面前“心悦诚服”的时候,才会用新的共识来取代旧的共识。 对一种社会理论、尤其是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论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法律规则的有效性基础问题。哈贝马斯和康德一样都没有把法律规则当作与上述规则并列的一种规则来加以讨论,他们也都强调道德规则与法律规则之间的特殊联系。但是,哈贝马斯在以下两点上不同意康德的观点。 第一,哈贝马斯不同意康德把他的法律理论仅仅建立在他的道德理论基础上,而主张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规则也需要通过诉诸道德之外的考虑而得到辩护。哈贝马斯把康德与霍布斯(T. Hobbes)进行比较,说霍布斯“把实证法和政治权力的道德含义都抽象掉,并认为在君主所制定的法律产生的同时,并不需要一种理性等价物来代替经过解魅的宗教法”,而“在康德那里,从实践理性中先天地引出来的自然法则或道德法则,则居于太高的地位,使法律有融化进道德的危险:法律几乎被还原为道德的一种有缺陷模态。”34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诸多行动者的行动的协调或整合需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协调社会中人们的行动取向,一是通过控制行动的结果来协调人们的行动。把法律归结为道德,是把法律仅仅当作前一种整合方式-所谓“社会性整合”-的手段,而没有看到,法律不仅仅告诉人们什么样的行动是道德上正当的,而常常也撇开人们的道德意识而用违反规则的利害后果来强制其采取某种行动;也没有看到,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这种作用对于社会系统的功能实现-尤其是现代经济系统和现代行政系统的高效运作-是非常重要的。哈贝马斯把这种整合称为“系统性整合”。换句话说,哈贝马斯强调法律不仅仅具有道德规则的向度,同时也具有技术规则的向度。与违反道德规则不同,违反技术性规则的结果是导致一种惩罚作为一个因果性事件随之而来。一个法律规则系统的存在,就是要使得一个违反规则的行动一定会带来惩罚性的后果,就像违反技术性规则一样。法律的这个技术性的向度,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它的道德向度。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法律的合法性不仅仅在于它具有道德的正当性,而且也具有技术的功效性。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不仅仅表现为技术上或功能上,而且也表现为价值上或文化上。尽管在我们的世界上,真正由单一民族、单一文化所构成的民族国家已经不多,但文化差异不仅仅存在于主权国家的范围之内(这要求民族国家内部的法律规则尽可能超越特定的世界观),更存在于主权国家之间-它们之间的诸多差异使它们还不能被归结为一个天下大同的道德共同体。也就是说,特定法律规则体系所适用的并不是普遍主义的“道德共同体”,而是具有各自历史经历(包括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历史经历)、价值观念和集体认同的“法律共同体”。这意味着法律规则之所以不能被归结为道德规则,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技术规则的向度,而且是因为它也具有伦理规则的向度,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区别于“规范”的“价值”的向度。 第二,即使就道德这一向度本身而言,哈贝马斯也与康德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哈贝马斯关于主体间性与规则之间内在联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在这里提出的。 哈贝马斯承认,康德虽然把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但实际上他已经超越了在他之前的自然法理论的传统:他不再把两者之间的联系看作是一种内容上的联系,而很大程度上看作是一种形式上的联系。康德看上去似乎仍然从“道德形而上学”中引出法律规则的有效性,但构成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已经不再是改头换面的宗教律令,而是对人的自主性和自律性-也就是人作为目的自身和自我立法者的地位-的强调。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意味着,康德作为法律之合法性基础的,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道德律令体系,而实际上是前面提到的科尔贝格所讲的“后俗成阶段的道德意识”,其最重要的特点是普遍主义:凡是对一个人具有约束力的,也应该是对于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当康德说“无规则即是无理性”的时候,他的直接含义虽然是强调科学“要求一种系统的、按照深思熟虑的规则变成的知识”35,但他不仅在这种主观的意义上、而且也在客观的意义上谈论“规则”:“规则,就其为客观的而言...,被称为规律。”36 康德把规律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规律,一类是自由规律,而两者的最重要共同之处,就是它们的普遍性:“自然规律是万物循以产生的规律,道德规律是万物应该循以产生的规律”。37 但哈贝马斯要指出的是,规则所适用的对象的普遍性,仅仅是规则的普遍性的两种含义之一。哈贝马斯把这种意义上的普遍性称作规则的语义的普遍性:它是用全称命题形式表述的规范性语句。但规则的普遍性还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即从规则的产生、运用和实施过程来看规则的特征。哈贝马斯把这种意义上的普遍性称作“程序的普遍性”,并主张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说,法律的普遍性不仅仅可以理解为其规则形式的普遍性,而且可以理解为其论证基础的普遍性,也就是获得一个特定法律规范或规范系统所要支配其行动的那些人们的主体间的普遍同意。哈贝马斯认为,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把自己不仅仅理解为法律的“承受者”,而也可以把自己理解为法律的“创制者”,也就是康德所说的自我立法者。 对法律的普遍性的这种看法,是哈贝马斯从其交往行动理论和商谈伦理学出发提出的“商谈的法律理论和民主理论”的核心内容。根据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商谈伦理学,“有效[gültig]的只是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有可能同意的那些行动规范。”38 哈贝马斯把这条原则称为“商谈原则”。“商谈原则”所提到的是任何行动规范,而商谈的参与者在不同情况下是有不同范围的。这条商谈规则也适用于对于法律规则的“有效性”或者“合法性”的论证,由此哈贝马斯从“商谈原则”引出他所谓“民主原则”:“民主原则应当确定,合法的立法过程的程序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原则规定:具有合法的[legitim]有效性的只是这样一些法律规则,它们在各自的以法律形式构成的商谈性立法过程中是能够得到所有法律同伴的同意的。”39“民主原则”像“商谈原则”一样把规则的有效性建立在规则支配其行动的那些人们的合理的同意或者说基于理由的同意基础之上,但民主原则具有这样一些自己的特点:把规则的种类仅限于法律规则;把商谈的参与者仅限于一个特定的法律共同体的成员;在商谈中所诉诸之理由的范围中包括实用的、伦理的和道德的三种类型,但以道德的理由为主;并且,除了所谓“论证性商谈”(主要适用于立法领域)之外,还有所谓“运用性商谈”(主要适用于司法领域),等等。
首先,自从英国哲学家彼得·文奇(Peter Winch)发表《社会科学这个观念》(1958)以来,遵守规则的问题就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文奇认为,社会现象区别于自然现象之处就在于构成社会现象的人的行动的特点是遵守规则而不仅仅是表现出规则性(regularities),而要了解规则的意义,进而了解行动的意义,就不能采取认识自然运动那样的客观观察的态度,而要采取主体间交往参与者的意义理解的态度。哈贝马斯从1967年出版的《论社会科学的逻辑》到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动的理论》中对“遵守规则”问题的研究,就是设法把日常语言哲学传统的这种观点与诠释学的观点沟通起来,用以回答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区别于自然现象的社会现象的研究何以可能? 第二,对于研究现代社会的人们来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帕森斯(T. Parsons)所说的“建制化个人主义”体现了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这种关系的矛盾性质:“一方面,个人应该与其个体化程度而成比例地获取更大的选择自由和自主性,另一方面,自由程度的这种提高,又被作了决定论的描绘:即使是对于建制化行为期待的刻板指令中解放出来,也被描述为一种新的行为期待-描述为一种建制。”40 这种“建制”也就是规则系统,它首先是指哈贝马斯常常讲的“系统”-包括经济子系统和行政子系统。摆脱传统社会的规则的强制之后,个体如果仅仅是在成为原子化个体的同时成为雇员、消费者、雇员、消费者、当事人等承担系统功能的“角色人”,那么,虽然看上去他面前有许多选择,但实际上这些选择都是被货币和权力这样的媒介所控制的。“这些媒介行使一种行为控制,这种控制一方面起个体化的作用,因为它针对的是由偏好导控的个人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它也起标准化的作用,因为它允许的只是在实现给定结构的向度中的选择可能(拥有还是不拥有,命令还是服从)。而且,个人的第一个选择就使他陷入进一步依赖的网络之中。”41 哈贝马斯之所以要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来研究行动者的规则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分化,一方面是为了从概念上把握现代社会的这种现象,另一方面是为了在理解这种现象的基础上克服这种现象。在他看来,那种被理解为在诸多已经被系统所事先构成的选择项当中进行明智的、自我中心的挑选的自我,仍然处于“俗成的认同”的阶段,也就是说仍然处于受到外在规则盲目支配的阶段。只有那种以超越特定界限的理想交往共同体作为参照系的“后俗成的认同”,才能自主地做出经得起交往同伴检验的基于原则的道德判断和基于价值的伦理决定。换句话说,哈贝马斯从主体间性的角度讨论规则意识或自我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是为了回答批判理论的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社会中真正自由的人格何以可能? 第三,在世俗化、价值多元化、同时权利体系又逐步普遍化的现代社会,集体生活之规则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既不能建立在宗教-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也不能被归结为规则系统的语义形式上的合理性和工具效率上的合理性。一方面,法律的统治要被公民认为是值得承认的(也就是说是具有合法性的),而不仅仅是被迫承认的,仅仅具有工具性效率是不够的。另一方面,在福利国家的条件下,古典的资产阶级法律的一些形式特征也已经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了。根据自由主义的法律范式,现代法律系统已经与宗教和形而上学相分离,同时也与不成文的、诉诸人们动机与态度的、常常与宗教和形而上学难分难解的道德相分离。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只能在于其所谓“形式合理性”-哈贝马斯通过对韦伯的法律观的讨论概括为三条:抽象而普遍的法规形式;在抽象-普遍法规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而得到确保的法律确定性;对法律系统用科学方法进行建构,以确保其意义是精确的、其概念是明确的、其自洽性是经过检验的、其原则是统一的。但是,在福利国家条件下,“权利”从古典的民事权利和公民权利扩展到现代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承认每个人都有劳动、医疗、教育、救济等等方面的平等权利。这不仅要求政府允许人们自由行动、保障这种自由不受他人(包括政府)的侵犯,而要求政府为公民提供实际条件、保障实际条件去实现这些权利和自由。这样,法律的形式从“如果-那么”的条件句形式(“如果这样行动,那么就处以怎样的处罚”)变成“符合某某条件的人将享有怎样的补偿”这样的调节性、目的性语句的形式;政府从维持市场运行秩序的公正无私的裁判者,变成通过干预市场运行过程、矫正市场运行结果而维护弱者利益的看护者。相应地,司法和行政部门也扩大了自由裁量空间,而不仅仅限于对意义明确、范围确定的普遍规则的运用和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合法性依据何在就成了问题。康德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对于主体性的强调,意味着他看到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要对人们具有正当的约束力,只能是当这种约束也就是人们的自我约束的时候。但是,康德还没有实现从“主体性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的“范式转换”。当所考虑的不是个体行动规则而是集体行动规则-尤其是法律-的时候,局限于主体性范式来思考主体的自主性或自我立法性,就可能把规则的约束力要么是归结为众多“小我”的多数意见(众意)的力量,要么是归结为一个“大我”(“人民”)的总体意见(公意)的力量。在前一种情况下,法律的基础是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多数人的当下意见,这样的多数人意见不仅很容易排斥少数人的正当权益,而且也容易违反多数人自己的真实利益。在后一种情况下,也就是用共同体主义的“大我”来超越自由主义的“小我”,则在哲学的层面意味着倒退到形而上学的思维,在社会学的层面意味着求助于自认为或者被认为是“大我”之代表的某个个人或某个群体。在这方面,历史已经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重要的不是在“小我”和“大我”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跳出这种执着于“我”或主体性的思路,把目光转向“我们”或者“主体间性”,转向具体的主体间交往网络或者社会建制。 换句话说,哈贝马斯之所以从主体间性的角度研究规则的正当性基础的问题,是为了回答“现代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辩护何以可能?”这个问题;而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哈贝马斯用他的“交往理性”概念来扬弃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交往理性之区别于实践理性,首先是因为它不再被归诸单个主体或国家-社会层次上的宏观主体。相反,使交往理性成为可能的,是把诸多互动连成一体、为生活形式赋予结构的语言媒介。这种合理性是铭刻在达成理解这个语言目的之上的,形成了一组既提供可能又施加约束的条件。” 42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本文开头引用的那两句话综合起来了:一方面,没有规则就没有理性;另一方面,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两者结合起来,结论是: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理性。
1 此文发表于《复旦学报》,2002年第5期 1 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杨一之校,商务印书馆,1991,129。 2 Jürgen Habermas: Vorstudien und Ergae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Suhrkamp, 1995, 12-3; Jürgen Habermas: On the Pragmatics of Social Interaction: Preliminary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lated by Barbara Fulner,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2001, 4. 3 以曹卫东、付德根翻译的《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为例。我手头没有该书的德文本,但根据我对哈贝马斯其它不少著作的德文本与英译本的对照,尤其是考虑到哈贝马斯的行动理论的主要理论渊源是英美哲学而不是德国哲学,把曹、付的中译本与其中收入的文章的英译本做一个对照,还是可以的。英译本译作“action”的每个地方,该中译本中几乎都译成“行为”。但在原作者并列使用或对照使用action (Handeln)和behavior (Verhalten)的时候,中译者就碰到麻烦了。比如第三章“后形而上学思想的主题”中“除了具有表达能力的肉体、行为、举止以及语言等范畴之外...”一句中,“行为”对应于英译本中的behavior,“举止”对应于英译本中的action。按照这样的译法,哈贝马斯那部主要著作的书名就该是《交往举止的理论》了。该书在第二编“实用主义转型”(收入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Philosophical Essays, [written by Jürgen Habermas, translated by William Mark Hohengarten, Polity Press, 1992],该编题目英译本为"The Turn to Pragmatics”,我以为译为“语用学转向”更妥当一些)中,第一篇论文的题目是“论行为、言语行为、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以及生活世界”,收入On the Pragmatics of Communication (written by Jürgen Habermas, edited by Maeve Cooke,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1998)的这篇论文的英译文的题目则是“Action, Speech Acts, Linguistically Mediated Interactions, and the Lifeworld"。中译者把对应于action和act的两个词都译成“行为”,非但取消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而且模糊了action(行动)与interaction(互动)之间的联系。中译本中那篇题为“个体化与社会化:论米德的主体性理论”的长文当中,用来翻译米德所使用的behavior一词的,都是“行为”,与用来翻译哈贝马斯的communicative action中的action的那个词完全一样。这样一来,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开始部分中对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与行为主义心理学之间关系的说明(本文后面会提到),就不是那么必要了。 4 哈贝马斯的这个观点并不是他的独创,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事所谓“行动哲学”(philosophy of action)研究的人们的一个共识。行动哲学是在维特根斯坦和赖尔(G. Ryle)等人的影响下形成起来的一个哲学分支。根据出版于1982年的一本对前一个十年中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著作的一位作者,行动哲学是该书综述的那个年代也就是七十年代相当活跃的一个哲学领域,而这个领域的两大问题之一是对行动的意向性的刻画(另一个问题是对意向性行动之说明[explanation]的刻画:“也就是说,要说明意向性行动是如何与不构成行动的那些身体运动相区别的。在这两种情况中都存在着行为;问题是要把意向性的行为与仅仅是身体运动的行为区别开来。在这里‘行为’被当作一个中性的词来使用,其范围既包括人们用来实施意向性行动的物理运动-比方说当一个人用点头来发出一个信号的时候,也包括那些并不构成行动的物理运动-比方说当一个人的头之所以上下点动仅仅是因为他正在酣睡的时候-也就是那些我们可以称作‘纯粹行为’的运动。要研究的问题是:是什么把意向性行为与纯粹行为区别开来的。”(Frederick Stoutland: “Philosophy of Action: Davidson, von Wright, and the debate over causation”, in Guttotm Flostad [ed.]: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 New Survey, Volume 3: Philosophy of Action, Martimus Jijhoff Publishers, The Hague/Boston/London, 1981, 46)在我翻译的这段话中,“行动”一词对应于原文的action,“行为”一词对应于原文的behavior。但实际上,重要的并不是用“行动”还是用“行为”来翻译action(Handeln)或者behavior(Verbehalt),而是我们要不要用中文来表达这两个术语所显示的那个概念区分,以及用来显示这个概念区分的中文表达是否要与现有的通常用法相一致-比方说,我们通常把behavorism译成“行为主义”,我们通常说“动物行为”而从来不说“动物行动”,等等。在哲学中(在其他学科中大概也这样),重要的概念区分常常是借助于学术翻译而引入的,所以在这方面翻译者-包括笔者自己-的责任实在不轻。 5 Jürgen Habermas: Vorstudien und Ergae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3; Jürgen Habermas: On the Pragmatics of Social Interaction, 5. 6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and 2, Zur Kritik der funktionalistischen Vernunft, Suhrkamp Verlag, 1987, 31. 7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lated by G. E. M. Anscombe,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4, 82. 8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and 2, 34. 9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81. 10 Saul A. Kripke: Wittgenstein on Rules and Private Language: An Elementary Expos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82, 60. 11 同上书,62。 12 同上书,99。 13 同上书,110。 14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and 2, 36. 在这里,哈贝马斯说米德感兴趣的是行动者的规则意识的形成问题。在该书的英译本中,该句被改成说作者他自己感兴趣的是这个问题。见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2,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Beacon Press, Boston, 1987, 20。考虑到此书的英译者经过作者同意而对原著做了一些改动,所以这个区别不能看作是译者的误译,而毋宁看作是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强调。 15 George Herbert Mead: On Social Psychology: Selected Paper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nselm Strau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56, 229. 16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2, 22。 17 同上。 18 Jürgen Habermas: "Individuation through Socialization: On George Herbert Mead's Theory of Subjectivity", in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Philosophical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Mark Hohengarten, Polity Press, 1992, 161. 19 同上书,171-2。 20 同上书,179。 21 同上书,182。 22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2, 174。 23. Jürgen Habermas: Faktizit?t und Geltung: Beitr?i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7,255。 24 同上书,311。 25见Jürgen Habermas: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 translated by Ciaran Cronin,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England, 1993, 6. 26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183。 27 同上书,184。 28 同上书,188。着重号是我加的。 29关于“构成性规则”和“范导性规则”的区别,见John R. Searle: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1969), 33-42. 30 见Jürgen Habermas: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164. 31见I.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Grudn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 (Suhrkamp, 1996), 46-51. 32 见Jürgen Habermas: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2-6. 33 Jürgen Habermas: On the Pragmatics of Social Interaction, 12. 34 Jürgen Habermas: Faktizit?t und Geltung, 590. 35 同上。 36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Werner S. Pluhar,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Indianapolis/Cambridge, 1996, 172. 37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36。见I.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Grudn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11. 38 同上书,138。 39 同上书,141。 40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149. 41 同上书,196。 42 Jürgen Habermas: Faktizit?t und Geltung, 17-8. |
|||||
| 文章录入:Angela 责任编辑:Angela | |||||
|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
| 最新热点 | 最新推荐 | 相关文章 |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管理登录 | | |
 |
粤ICP备05083455号 Copyright 2004-2005 CulChina.Net 主办:深圳大学文学院·传媒与文化研究中心 站长:孙海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