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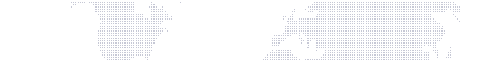
| | 网站首页 | 文章中心 | 学术动态 | 资料下载 | 建议留言 | 文化论坛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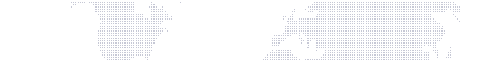 |
| 您现在的位置: 文化中国 >> 文章中心 >> 文化前沿 >> 文化理论 >> 文章正文 |
|
|||||
| 电视 声音 | |||||
| 作者:里克·奥…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12-13 | |||||
|
一 对雷蒙·威廉斯来说,“核心的电视体验是流动的事实”。2威廉斯拒绝在电视系统之间做出区分,他认为“在所有发达的广播系统中,独特的组织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独特的经验,都是一种序列的或流动的组织或经验。于是这种有计划的流动的现象,便可能把广播的特征同时限定为技术和一种文化形式。”(p.86)威廉斯发展了一种与安德列·巴赞的电影现实主义惊人地相似的目的论解释,3并进一步勾画出英国和美国广播电视中似乎是必要而且自然的流动的发展,强调“从作为节目编排的序列概念向作为流动的序列概念的重要的转移”(p.89)。威廉斯通过本体论的反思,最终把流动的概念与“电视体验本身”(p.94)联系起来,好象技术本身足以保证各种跨越文化和产业体系的境况的相似性。 流动的概念已被证明极为适合分析美国电视。我打算批评的不是这个概念本身,而是流动是电视的总体特征的主张。我认为流动的概念依赖于电视的特殊文化实践,不参照相对应的家庭流动的概念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它,声道尤其承担了协调这两种流动关系的任务。威廉斯在承认英国和美国电视实践以及商业和公共系统的显著差异之时,自己为这种分析打好了基础。但在每一要点上,他满足于根据这种媒介的真实本性的实现程度来解释这些差异。英国人“落后”于美国人,公共电视落后于商业电视,但都在向一个方向走,因为它们都带有同样由技术决定的本质。 从这一点上看,新出现的全国广播系统每晚提供一套节目,根本没有发展到足以支持一个充分运转的流动;但给它时间,流动最终就会出现。然而,那些与威廉斯的分析所依据的英国和美国的广播业不同的广播或有线电视系统,即那些实行并维持节目编排限制,并特别排斥流动全面发展的系统,又会怎样呢? 这里有两种非常明晰的替代模式。我们或者像威廉斯那样,根据特定的电视系统发展阶段的差异来解释这种流动差异,或者承认这种流动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与特定文化限定的电视功能的差异相对应。暂时我想提出以下假设:流动取代不同节目编排的范围是,(1)使竞争观众主宰广播的情境;(2)电视收入随收视的增长而增长。简而言之,流动不是与电视体验本身有关——因为不存在这种单一的体验,而是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中的观众的商业化有关。这样我们在东方集团国家发现了最低水平的流动,那里节目编排被小心地控制并以标准的次数在适当时间播发。在像法国这样的高度社会化的西欧国家,电视由准政府、准独立的机构制作和编排,流动的水平多少高一些,但仍然明显地受国家决策的限制。英国电视在创办时像法国电视一样,但它向商业化屈从的速度却快得多。那里的情况仍然是复杂多样的,但当两个BBC频道越来越效法两家商业电视台,并且整个系统越来越模仿美国电视时,流动的程度迅速增大。甚至在美国内部,流动也截然不同:公开并直接地争夺观众的广播网培育了高水平的流动,而使命截然不同的公共频道和地方频道维持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流动系数。但让一个大城市公共频道过分注意收视率(像在纽约、芝加哥或洛杉矶那样),流动就又开始了。 最高度流动的国家也是那些有最高度发达的收视评估系统的国家,这不应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流动与利润动机和观众商品化联系在一起。与销售节目给观众的电影业不同,商业广播电视把观众卖给广告商。正如电影院孕育了一个致力于评价其产品质量和魅力的复杂产业,商业电视业创造了一种先评价数量后评价质量的方法。电影的二级产业首先集中在影片本身,并因此主要把自己表现为报纸和无线广播评论,表现为奥斯卡和其他奖项;但电视的评估服务更关注电视的非常不同的产品:观众本身。像电视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一样,电视观众评估几乎全都用数字来表达。评估工具中最重要的是A.C.尼尔森公司出版的收视评估。当然对于尼尔森实际测量什么总有一些不同看法。虽然尼尔森声称它的计数器/日记组合能够清晰地显示出电视观众的情况,但许多研究都已经提出尼尔森的收视评估模式需要做些修正。 遵循鲁滨逊和艾伦的早期研究,41972年美国卫生局长关于电视和社会行为的报告中的许多部分都直接谈到电视观众对电视节目注意力的问题。5福克斯(Foulkes)等人发现,如果孩子们在看电视时有机会享受游戏、书、玩具等吸引人的东西,眼睛接触就大大下降,这并不令人惊奇。6罗修托(Losiuto)发现列在收视日记上被“看过”的节目有34%实际上是间断地看的,或者只是在回答者做其它活动时(按频率的次序:工作、家务、进食、说话、阅读、照料孩子、缝纫、照料个人、爱好和家庭作业)无意中听到的。7 这些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包括对被要求回答收视情况问卷的家庭录像。由比奇特尔等人做的这个研究揭示出,在报告的多数收视时间中,家庭实际上并没有在看——虽然电视可能开着。8用实际电视开机时间的百分比表示,结果仍然是惊人的:电视开着时,节目收视率实际上从55%(广告)到76%(电影)。 这个研究使作者得出如下结论:“普遍而言,数据指明收视和不收视的不可分割的混合是看电视行为的普遍风格。”9确实,《卫生局长的报告》第四卷的编辑杰克·莱尔感到有必要为他的引论性评论加一个附录,反映商业和学术研究中过高估计收视时间的持续倾向。他指出,注意的时间不限于眼睛接触的时间,但调查却继续以它仿佛就是那样行事。10只是最近才有一些分析证实莱尔的直觉。11 尼尔森的评价体系以及当前一些电视美学的研究认为,主动收视是观众(spectatorship)的惟一模式,但有日益增长的数据表明间断性的注意实际上是电视收看的主导方式。这种间断性观众的实践影响节目决策和声道的构建。既然电视网战略家的目标不是增加观众(viewership)而是提高收视率,既然那些收视评估计算的是打开的电视机数量而不是观众数量,那么只要保持电视机开着电视业便有既得利益,即使电视机前并无观众。 于是声道开始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为了在所有电视观众不在房间或很少注意时让那些电视机开着,声道必须发挥一些特殊的功能: (1)必须让听众确信即使图像不可见时,声道也提供足够的情节或连续的信息。例如,必须能够从厨房里跟上肥皂剧的剧情或者在卫生间里跟上足球的比分。 (2)必须有一种使任何真正重要的东西都由声道提供线索的意识。这个概念部分来自于持续地将电视节目等同于实况转播;它在全天实况转播流动事件中达到顶点,如水门事件听证会、选举结果或奥运会那种长时间的体育赛事。如果我们能确保在重要时刻被召唤回来,那么甚至当我们无法留在观看距离之内时把电视机开着也是值得的。 (3)通过单个节目或连续节目所提供的声音和材料的类型必须有可辨认的连续性。无线电视广播电台通过整天保证同种风格的音乐或谈话做到这一点。电视则通过全天(至少到午后晚些时候儿童系列节目开始时)从一个假定妇女关注的问题转向另一个妇女问题,或者在周末下午从一个体育节目转到另一个体育节目来做到这一点。尽管这主要是一个负面的标准(如果连续之中出现中断,电视机有被关上的危险),但应该承认整个系统基于否定性:目标不是让任何人仔细地看电视(像在某些国家和我所在大学的频道一样),而是让人不至于把电视机关掉(这是尼尔森所报告的东西,因此也是决定电视网收入的东西)。 (4)在流动中,声音本身必须不时地提供人们渴望的信息、事件或情感——时间、天气、学校关门、新闻短讯、颁奖、情感危机,等等。甚至直播的新闻、体育和电影频道也通过或多或少有规律地安排最新消息,或者以一种节目的简短形式不断打断另一种节目解决了这个问题。CNN头条新闻分布于整个正常的WTBS节目编排是这种做法最明显的例子,而奥运报道中间插播新闻摘要和在标准的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间插播奥运最新消息,则是这种做法普遍化的充分证据。这个原则对于虚构节目与现实报道一样真实。一个以诡诈、英雄主义、昏厥、真爱、赤裸的爱和赤裸的真理的沉默形象为特征的节目,仍然需要这些重要事件的可听的证据来维持间断性观众的兴趣。 简而言之,由于两个打开的电视只有一个实际上被观看(这是上述各种研究提出的数据的约略的平均值),所以在威廉斯所说的“节目流动”和我将称之为“家庭流动”[householdflow](充分认识到这第二个流动很可能也发生在酒吧、学生会、兄弟会会所、医生的候诊室,或者工厂或商业场所的休息室12)之间,声道变成了主要的调和方式。早些时候,我提出流动的概念不是电视技术的自然的伴随物,而是一种特殊消费形态的结果。那个相当隐晦的论点的重要性现在明显了:在以观众为最终商品的体系中,在观众的规模不是以实际看电视的人数而是以打开电视数来衡量的体系中,电视的组织方式必须与它所依赖的家庭流动相协调。这样,节目编排被分割成短节,这些短节体现了任何陷于家庭流动的人的有限的持续观看时间。同时,重新强调声道的信息承载能力,而声道在开机的多一半时间中保持与观众接触。用另一种方式说,流动的在场不像威廉斯所说的那样依赖于频道间的竞争,而是依赖于与家庭流动竞争。在节目流动最小的系统中,电视和家庭之间有一种类似的低水平的互相作用。在许多全国系统中,电影占据了整个晚上的广播节目编排,既不受中断也不受插播广告的妨碍。在这种系统里仍家庭流动和电视节目编排之间的关系与家庭流动和影院电影展播之间的关系相似:当到了看电影的时间时,你离开家。13这绝对不是这个国家看电视的方式,因为节目流动的发展与家庭流动和电视节目编排的交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测量体系混淆观众与听众的倾向为这种联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4这一过程最明显的结果是使声道负有确保任何潜在听众都不关电视的特殊责任,从而确保众人皆知的收视过高的报告得以继续。 二 美国商业广播网已经为电视声道发展了以下六种重要的功能和技术。 (1)标定(labeling)。在竞争引起高水平流动的地方,典型的电视肌质是短节分割。商业广告、《早安美国》、晚间新闻、杂耍大观、答问比赛(quiz)节目和体坛广角等显然都是如此。在虚构的叙事节目中虽然可能不那么明显,但同样的片段化仍然发生作用。例如,《达拉斯》不仅按照一种小说性的阐释来组织,而且也围绕着一套复杂的题目来组织,它们对一些观众来说是通过角色体验的(如J.R.,鲍比,苏·艾伦,帕姆,克里夫,艾丽小姐等),而对另一些观众来说则是按主题来体验的(如性、爱、权力等)。用简·福伊尔的话来说,由于《达拉斯》作为“没有封闭的分割”呈现给我们,所以并不期望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情节的线性、方向性和目的性。15相反,它从一开始就承认我们根据其他方面来选择我们注意对象的愿望。观众对一个给定的好莱坞电影场面的注意程度可能大体上依赖于那个场面在解决情节困境上的重要性,而对一个给定的《达拉斯》场面的注意还要依赖于表现的题目和角色。在承认这种差异当中,我们可能说对经典好莱坞叙事的注意一般是目标驱动(goal-driven)的,而对美国电视叙事的注意主要是节目单驱动(menu-driven)的。对于在电视前稳坐的观众来说,节目单通过图像清楚地显现出来。但对于眼睛没有沾在荧屏上的一半观众来说,声道必然用来标定节目单的内容。 (2)强调(italicizing)。约翰·埃利斯在《可视的虚构》中指出,“与在影院中看电影情况相同,几乎没有机会在‘明天’或者‘下周某个时候’捕捉一个特定节目”(p.111)。不论由电视传递的事件是否是直播,居家观看的观众对电视经验本身的感受都是直播的。正如摄像机不得不在现场记录活生生的新闻事件,潜在的观众必须保证当重要的东西发生时她的眼睛在电视上——否则可能会永远错过它。不无矛盾的是,甚至录制的虚构节目比一个直播的新闻或体育节目更是如此,后者会在晚些的新闻中报道,而对于未能在适当时间回到荧屏的人来说,他会永远失去观看已在进行的虚构事件的机会(我怀疑,与预期相反,用录像机做时间转换无助于减少这种潜在的损失感。根据我的经验,时间转换不是用于那些间断地观看的节目,而是用于那些观众自始至终聚精会神地观看的节目)。 典型不可逆转的广播电视的展示情境提供某种与更广范围的不可逆转的、不可编排的形式的总的联系,所有这些形式都通过以新出现的物质确保重复的、准仪式的近似的同一性来补偿不能返回去再看同样的东西的遗憾(口头史诗和田园形式这样做,系列小说、喜剧连环画、广播和电视剧也这样做)。电视节目编排本身因此有不可逆现实的特性。我们不能决定什么时候看一个特定类型的节目,也不能决定什么时候一个特别事件会在节目中出现。我们必须在不间断的基础上注意节目以确保我们不会错过什么东西,其方式就像一个看小孩的人自动地监控她/他负责的房子和孩子的情形。于是这里就出现了声道的“强调”功能。我们不能总是把眼睛盯在电视机上,但我们已经学会听某些声音的线索,它们会说,“这是你一直在等的那部分,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是一个很棒的比赛,这是你播到的节目播发基本内容的时间。” 新闻播音员讲话;他的高度客观性要求一个中立的形象——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不寻常,没有分分、天天、月月的变化。但声音不断变化——实际上我们正是由于这变化而一直在收听,甚至当我们无法收看时,我们还在收听。但这些语言的强调(verbalitalics)用于什么目的呢?它们一律用于召唤我们注意图像,让我们敌我们不敢错过的东西正在发生;简而言之,它们让我们注意到惊人的事物。词是精心选择的,因为它揭示声音的强调功能有助于确定哪个值得看而不只是听的程度。电视直接服务于生活观念,其中的日常事件难以察觉。我们的日常流动被视为生活的平淡的、可听的、持续的填充物,所以只有在它指向惊人的事物时才获得意义。这种惊人的事物我们肯定不能参与,但如果看到,能够给我们生活以意义。通过对每个节目的某些部分加以强调,声道就会把我们引回到图像,回到电视机本身,如此就把我们永远地置于惊人事物的一种美学和一种意识形态之中。 (3)声音解释学(soundhermeneutics)。与其它所有吸引人的东西相比,声音有一种隐蔽的优势,因为在西方世界声音几乎总是被认为是不完整的;它似乎要求与可见的源头相认同。电视已经使我们习惯于从我们的视听投资上获得一种高水平的回报。我们非常确信,只要我们从厨房足够迅速地冲进屋子里,电视会向我们显示声音的源头。我们习惯于这种安排所保证的整体感。当我们听到一个声音时,我们发现它的源头在屏幕上,这样给我们一种在场感和解决感。 把这种情境与普通的电影安排相比是很有启发性的。在《耶鲁法语研究》的《影院/声音》卷的一篇文章中,我证明画外音,或者更精确地说,没有可见源头的声音(米歇尔·舍昂称为“幻听声音”[acousmaticsound]),是怎样产生一种“声音解释学”的:声音提出“在哪里发生?”这个问题,一旦辨别出来源,对此形象最终回答“在这里发生!”用另外的话说,声道利用与观众的渴望相符或者不符的摄像机来引起观众的介入。 但在电视中,观众/听众取代了摄像机在声音解释学中的位置。当声音挑起了我的好奇心,通过将我的注视转到屏幕上,我几乎肯定能得到满足。我自己进行控制,而不是依赖于可能让我等着看什么在制造那响声的摄像机和导演。通过抬起我的眼睛,扫视屏幕,我自己发现了声音的源头,如此体验了它暗示的整体。 电影观众对他们控制正在看的电影的能力几乎很少有错觉,而电视观众不同于电影观众,他们倾向于相信他们对图像有控制力。但实际上引起声音解释学的“标定”和“强调”受到严密控制,并且遵照规定的路径,因此为电视主体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电影主体的意识形态定位,其自由的错觉力图掩蔽得更彻底。 (4)内部观众。当我们听到一个喜爱的明星的声音时,我们转向屏幕以完成我们对明星在场的感知。那个明星可能是一个演员、一个政治人物、一个体育英雄,或者只是广告片中的可爱面孔。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我们选择追踪的屏幕的声音的种类。一个更普通的情况从我们这里剥夺了那种权利:我们听到的不是屏幕上一种特殊的视觉存在的标记,而是别人认为一个重要的现象在屏幕上发生的一个标记。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技术比内部观众的几乎永久的在场对电视的总体的内在动力有更大的影响,这种内部观众有时在图像上,但总是在声道上。声道一般用来发表编者意见,甚至当它与实况图像相匹配时也不例外。体育赛事实况实际上是由很少的实况音响效果伴随的实况图像,其他的声道部分都用于画外评论;甚至同步声音对话的短片也只是播音员的讲话的转播,如同历史小说中的直接引文。 不论图像多么生动,声音继续充当介绍,充当评论——简而言之,充当画面的观众。声道执行它的“强调”功能,发挥有价值取向的编辑功能,比画面本身更好地识别画面中足够惊人、值得间断性观众密切注意的部分。理解电视的视听综合的有效模式因此不是那种适合于真正生动地呈现的模式。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一事件的观众同时听到和看到场面的两个部分。形成对比的是,电视观众对生动事件的眼光一般经过声道的过滤,声道为一种插在其间的内部观众而说话。这是多数演播室偏好的安排,当然这不是偶然的:摄影机从演播室观众的头上看观众正在看的场面。无论声道传送的是同期录制的演播室掌声还是只是一个添加的笑声,声音被处理得让我们确信掌声或笑声从一个比场面本身离我们更近的地方发出。人们吃惊地注意到,新闻播报和体育最新消息节目——更不用说“早安美国”和其它早餐秀——包括内部监视器,内部监视器通常位于播音员的身后,这样播音员就不得不稍微离开观众一点来看,以看到在屏幕上的监视器。这么做播音员就清楚地在视觉上建立了电视的内在观众的总的形态:为了到达允诺的画面,我们必须看过去、看穿或者环顾内在的观众,他们可能看得见也可能看不见,但他们总是被听到,总是准备告诉我们对那些画面我们“需要知道”什么。 最普通的内在观众是众人皆知并经常被用到的:新闻播音员、体育播音员、播音室观众(或其替代物笑声声道)、体育场群众、广告产品的使用者。一个更复杂的情况发生在越来越频繁的“外景叙事”(locationnarrative)当中(与“播音室叙事”相对,后者有实际在场或声道暗示的观众)。例如成人肥皂剧或者动作片(actionshow)——基本上限制在较晚的黄金时间——这些外景叙事看起来、听起来更像好莱坞的电影而不是其它电视作品:播音员、演播室观众和满足的消费者没有进入声道,似乎在所有电视节目中,只有他们完全不受内部观众的影响。但这些节目经常独特地围绕着一系列高度可视的事件和人物确立,别的人物充当他们的观众。例如在《达拉斯》中,雷和唐纳扮演了节目的“良心”角色,更多地对J.R.的恶作剧提供一种模范的道德反应,而不是引发他们自己的活动。J.R.的各种情人——特别是梅里李·斯通——扮演对他的不道德幸灾乐祸的相反角色。贫穷、漂亮的阿夫顿对于克利夫·巴内斯和他的雄心勃勃的愚笨言行不过是一个不变的观众。 当一个节目不能很顺畅地把内部观众配进它的计划,或者当需要更大的强度时,音乐提供了解决的办法。在某些方面,外景叙事的音乐似乎在好莱坞停止使用的地方开始,但我们不应被这种表面的类似所欺骗。确实,两者都是节目性的,但电视音乐所取的路径更具评价性,更有可能让另一个屋里老练的听众识别出哪怕是最微小的事件。电影音乐的乐章长而且笼统,与电视音乐对每一个高低点的注意形成对比。正如笑声声道必须保证每分钟一定数目的笑声,外景叙事的音乐也必须为在厨房中努力跟踪节目、不能为任何东西都冲来的小两口提供一个详细的道路图。虽然方法不同,结果却一样:声道提供了引导外部观众收看选择的内部观众。 (5)声音进展(Thesoundadvance)。在我已经提出的论点中存在一个显著的矛盾。一方面电视倾向于生动的或者“磁带上生动”的呈现,以内部观众对内部场面在真实时间中做出反应;另一方面电视声音发挥着召唤间断性观众了解声源或者了解它的发声原因的作用。问题很简单:将来的观众怎样才能保证看到引起观众掌声的场面——如果这掌声是由在掌声之前的活动引起的,从厨房冲进来或者从日报上抬起头来的外部观众可能因此看不到这个场面?画面展示着,录了音的观众反应着,但当电视观众看的时候,场面可能已经消失了。从逻辑上讲,这种情况本该发生,但实际上我们经常发现一些非常不同的事。为了服从其本身的逻辑,广播网电视一般逆转自然的进展。在场面揭示之前,录了音的内部观众必须作出反应,引起外部观众的注意。表面上,这种安排听起来是荒谬的。观众对他们没看到的东西怎么做出反应呢?他们不能,而这正是要点:内部观众必须对我们外部观众还没有看到的东西做出反应。因此,在内部观众目睹有关场面的时刻与场面揭示给外部观众的时刻之间必须有一个延滞。 在播音室录音中,这是极其简单的。最明显的便捷方法是在主持人出现之前在观众前面挥舞“鼓掌”卡就行了。把“我们表演的明星”从旁边带上来可以产生类似的效果,这样一来,播音室的观众在他上屏幕前就看到并认出他。假如一个电视表演者被扩音器的电线绊倒,引起播音室观众的自发的大笑会怎样呢?没问题,因为作为一个受过电视训练的女演员,表演者无疑会在有伤尊严的位置上呆上几秒钟,扮鬼脸时间长得足以确保摄像机以及家庭观众抓拍到她的不雅的,但值得报道的不像样的失态。通过运用观众提示卡、聪明的背景设计或混合图案、节目的音乐、即时重播等等,间断性观众获得返回电视机并见证兴奋场面的时间,因为从外部观众的角度来看,声音之后出现的是作为声音效果的原因。 这种逆转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早些时候看起来像自然因果关系的东西(物体引起声音)现在有了般的气氛(反应生成行动)。声音与图像向后呈现,把随意的听众也转变为观众。把听众插入观众,把家庭流动插入电视流动,就这样通过声音与图像之间的被接受的逻辑与时间关系的逆转而发生。声音本是一种反应,必须被重铸为一种预言,这样我正被唤起注意的图像可能反而看起来好象是特别为我制作的。 (6)话语化(Discursification)。好莱坞叙事电影主要是非话语性的。它拒绝承认观众的在场,相反,它让观众采取窥视者(voyeur)的立场。这种立场依赖于一种可靠的、连续的注意程度。电视的观众是不可靠的。电视与周围的注意对象竞争,就像它做广告的产品所做的竞争;这样在总体上它就更具话语性,向观众致意并把观众卷入对话,叫他们看、听,参与那些供我们看的东西。 用声音召唤间断性观众返回电视机前对声音和图像的话语性都产生广泛的效果。对于电影观众来说,《今夜爱我》中曼努里安有名的跌落花瓶的爆炸是一个玩笑,一种夸张,或者一种错配,但在电视上类似的声响事件可能是让观众回到电视旁边的呼唤,一种把作为故事(histoire)的声音(告诉我发生着什么的声音)转到作为话语(discours)的声音(告诉我去看以发现发生着什么的声音)的呼唤。以类似的方式,美国电视新闻越来越转向呈现性,把由中立的播音员和高密度表现性的声音组成的初级水平与由高密度图像和从属的声音构成的二级水平融合在一起。于是,真实矛盾地被认为是双层的:播音员告诉我们真实(今天埃尔巴火山又爆发了,产生的熔岩摧毁了两个村庄,切断了三条道路,夺走了至少十条生命),但那是历史真实,一个发生在别处与他者有关的事件,因此与我们无关。但是如果我能看到事件,如果他们能够从他们的历史性的位置转到一个新的能为我播放的侧面,那么他们能够改变形式和功能,成为一种话语回路的一部分。我们电视更深层的、矛盾的真实是这种世界的话语化。不仅眼见为实(电视观众的较早假设),而且为我们收集的图像给我们一种平淡的历史叙述不太可能给我们的感觉。只有声道上先前的播音能让那些图像看起来是为我们做的。 即时回放可能是这种话语综合症最终的例子。假设我在厨房里喝啤酒。突然我听到欢呼声,一个播音员正为投掷的完美和抓球的杂技般的优美惊呼。直到这一点,比赛者都在根据客观的、非个人性的比赛规则去赢得比赛。他们可能一直为体育场观众或者甚至为电视观众作秀,但当他们比赛时,他们的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打败对手。现在,当观众喊叫时,我从厨房冲出来赶上剧尾,但无疑它作为一个比赛永远结束了,完成了,过去了。不过即时回放帮了大忙。它正好向我展示了我刚从厨房出来要看的东西。借助多重摄像机和各种慢动作,它找到最不平凡的角度,或者揭示使抓球成为可能的主动干预的角度。因此重放与播放的关系,与再现过程与现时的关系相同。无形式、不解释、缺少方向,现时只有在再现的过程中取得意义——它的“为我性”(for-me-ness)。对电视的记忆因此不是对整个比赛的记忆,而是某种传播的自由(啤酒、电话、厕所、报纸等)与矛盾知识的结合。这种知识认为比赛是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镜头为我总结出来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把我唤到电视机那里去的同期声音在即时重放出现时已经消失;声音已经消耗在呼唤游荡的观众之中。通过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把一种特制的图像与特别想看这个图像的观众聚在一起,声音成功地把观众与图像都结合在它所指引的话语回路中了。一方面是电视流动,另一方面是家庭流动。只有当声道成功地把图像与观众聚在一处,它才能完成这一使命。由于肩负把我唤到图像的任务,声道调遣每一种武器:标定、强调、声音阐释、内部观众、声音推进。但最终的结论,同样是最终的目标,仍然是持续由声道所培育的观念:电视图像正是在我需要它的时间为我制造并播出的。 注释: 1JohnEllis,Visiblefictions:Chiema,Television,Video(LondonandBoston:RouteledgeandKeganPaul,1982),特别是第八章“BroadcastTVasSoundandImage,”pp.127-44. 2RaymondWilliams,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NewYork:Schocken1974),p.95. 3对巴赞电影史方法的批评,请见JeanlouisComolli,“Techniqueetidéologie:caméra,perspective,profondeurdechamp,”inCahiersducinéma,(MayJune1971ff.):299、230、231、233、234-235、241。 4JohnP.Robinson,“TelevisionandLeisureTime:Yesterday,Todayand(Maybe)Tomorrow,”PublicOpinionQuarterly33(1969):210-22;C.L.Allen,“PhotographingtheTVAudience,”JournalofAdvertisingResearch5(March1968):2-8. 5TelevisionandSocialBehavior.ATechnicalReporttotheSurgeonGeneral'sScientificAdvisoryCommitteeonTelevisionandSocialBehavior,ed.EliA.Rubinstein,GeorgeA.Comstock,andJohnP.Murray(Washington,DC:U.S.GovermmentPrintingOffice,1971). 6D.Foulkes,E.Belvedere,andT.Brubaker,“TelevisedViolenceandDreamContent,”TelevisionandSocialBehavior,vol.5,pp.59-119. 7LeonardA.LoSciuto,“ANationalInventoryofTelevisionViewingBehavior,”TelevisionandSocialBehavior,vol.4,pp.33-86. 8RobertB.Bechtel,ClarkAchelpohl,andRogerAkers,“CorrelatesbetweenObservedBehaviorandQuestionnaireResponsesonTelevisionViewing,”TelevisionandsocialBehavior,vol.4.pp.274-344. 9同上,第298页。这项研究把许多同时进行其它活动的个体包括在观众之列,因此可能过高估计了主动的观众的数目,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使用的类别是(1)参与,积极地对电视机做出反应或者根据电视机中的内容对别人做出反应;(2)被动收视;(3)看电视时同时活动(就餐、编织等);(4)摆出看电视的架势但阅读、谈话或者注意别的事情而不是看电视;(5)在电视的收看区域,但取的不是看电视的位置,以至于需要转过来才能看电视;(6)不在屋时且看不到电视或者不受视觉内容的冲击。类别1-3被认为是“收看”而类别4-6则不是收看。把这个方法与JonBaggeley和SteveDuck在DynamicsofTelevsion(Westmead,England:SaxonHouse,1976)中提出的更传统的类别做比较是更有启发性的。他们提出的最低水平注意(“完全被动地卷入想象的纯粹新奇价值”p.86)对应于Bechtel等人提出的理论图示的第二层次。后者列出不少于四种低层次的注意。 10JackLyle,“TelevisioninDailyLife:PatternsofUseOverview,”televisionandSocialbehavior,vol.4,pp.26-28. 11对人很有帮助的对该文献的评论见GeorgeComstock,StevenChaffee,NatanKatzman,MaxwellMcCombs,andDonaldRoberts,TelevisionandHumanBehavio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8),pp.141-72.另外特别要看HelenLeslieSteevesandLloydR.Bostian,DiarySurveyofWisconsinandLllinoisEmployedWomen,Bulletin41(Madison:UniversityofWisconsinextension,1980).这个研究收集的数据,构成了即将出版的SamuelL.Becker,H.LeslieSteeves,andHyeonC.Choi的名为“TheContextofMediaUse”论文的基础。这些数据揭示出工作女性只在她们35.2%的“收看”时间中看电视而不同时做别的什么活动。另见电视观众公司的各种报告,它们是马尔科基金会1979年在福特基金会帮助下建立的Nielson与Arbitron的收视测量(Audimeter)方法的替代。根据一个初步的报告,被调查的全部观众的49%说在“收视”时间有另外的活动,这些人中有42%说他们被他们主要的另外活动从收视中分心,即使只有黄金时间的收视被调查。见EizabethJ.RobertsandPeterJ.Lemieux,AudienceAttitudesandAlternativeProgramRatings:APreliminaryStudy(Cambridge,MA:TelevisionAudienceAssessment,1981).可能从虚构的角度对间歇收视的最好的反思是由MichaelJ.Arlen的短篇小说“GoodMorning”提供的。见TheViewfromHighway1(NewYork:Ballantinebooks,1976)pp.13-19.促进间歇收视格局的早期广播网策略的历史情境的一部分包括在WilliamBoddy未发表的论文“TheShiningCenteroftheHome:OntologiesofTelevisioninthe‘GoldenAge’.”Boddy指出间歇无线广播听众收听的程度成为电视观众特质(spectatorship)的早期模型。 12关于家庭之外的收视,见DafnaLemish,“TheRulesofViewingTelevisioninPublicPlaces,”JournalofBroadcasting26(fall1982):757-82,andViewingTelevisioninPublicPlaces:AnEthnography,unpublisheddissertation,OhioStateUniversity,1982. 13已有的跨文化数据充分支持这种观点。在TheUseofTime:DailyActivitiesofUrbanandSuburbanPopulationsinTwelveCountries,ed.AlexanderSzalai(TheHague:Mouton,1972)中,RobinsonandConverse报道了下列数字。我把它们重新分为宽泛的政治/经济范畴: 每天收视的总分钟数收视作为首要活动收视作为次级活动次级活动在总体中的百分比东欧5951814西欧88701821美国129923729 虽然这些数字是60年代晚期收集的,需要更新,但它们清楚地显示间歇收视与美国以广告为导向、以收视率为基础的模式明确相关,而在西欧,美国的这种模式只是部分地受到抵制。应该指出,在没有被回答者按等级划分的同时性活动的情况下,这项调查把每个活动划分为一半首要的、一半次级的,便把对收视的过高估计确定为严格的首要活动。关于资料收集的信息,请见Robinson,“TelevisionandLeisureTime,”pp.210-22. 14我反对把所有电视系统用在一个单一的和无差别的“电视经验”中,因此我将论证美国的广播电视必须被分成时间段,每个段对应于一个与家庭流动不同层次的竞争。早在194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出版物《电视观众研究》(纽约:CBS,1945年)认为“电视的白天节目……可以构建,使得从中取乐不必全神贯注。需要眼与耳全神贯注的节目应该被安排在晚间,那时观众感到应该娱乐和放松。”(第6页)在注释四中提到的阿兰研究提供了以下数据,分解成每日时间段: 合计早晨下午晚上每周用电视机的小时数31.83.59.718.6开着电视但不看12.81.84.56.5不看电视占开着电视时间40524735的百分比 间歇观看百分比最低的时段既与家庭流动竞争最低的时段对应(孩子睡觉了,家务做完了),也与以自满的、目标驱动的叙事节目的最高商数为特征的时段对应。间歇收看比率明显高的白天时段传统上是与妇女儿童观众相连的。Szalai等人的报告显示美国家庭主妇(38%)把看电视作为次级活动的人比受雇男性(18%)高两倍还多。最近,Roberts和Lemieux发现年龄在18岁至39岁的女人是最不可能注意节目的群体(只有31%的18岁至39岁的女性在一个节目的全过程中呆在屋里)。这些数字惊人之处是Roberts和Lemieux只在黄金时间做调查(这样就省略了妇女的高间歇收视时段),并且Szalai等人的报告显示受雇女性电视收看中的36%是次于其他活动的——只比家庭主妇少2%。这些数字指明了美国广播及其消费中两种相关但分开的现象: 1)电视网的节目选择与家庭流动的格式密切相关,产生一个电视流动的系数。这个系数与其他全国系统比是高的,但在晚间时段是下降的。 2)文化格局使成年女性比成年男性有一个高得多的间歇。 这两个假设可能与TaniaModleski'“TheRhythmsofReception:DaytimeTelevisionandWoman’sWork,”inRegardingTelevision:CriticalApproaches—AnAnthology,ed.E.AnnKaplan(Frederick,MD:UniversityPublicationsofAmerica,1983),pp.67-75同样需要进一步研究。 15JaneFeuer,“TheConceptofLiveTV:OntologhyasIdeology,”RegardingTelevision,pp.15-16. 16RickAltman,“MovingLips:CinemaasVentriloquism,”YaleFrenchStudies60(1980):67-79.MichelChion,Lavoixaucinéma(Paris:CahiersduCinémalEditionsdel'Etoile,1982). |
|||||
| 文章录入:DarkBlue 责任编辑:DarkBlue | |||||
|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
| 最新热点 | 最新推荐 | 相关文章 |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管理登录 | | |
 |
粤ICP备05083455号 Copyright 2004-2005 CulChina.Net 主办:深圳大学文学院·传媒与文化研究中心 站长:孙海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