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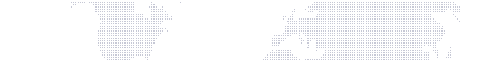
| | 网站首页 | 文章中心 | 学术动态 | 资料下载 | 建议留言 | 文化论坛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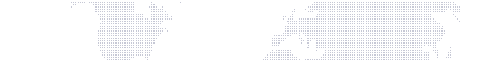 |
| 您现在的位置: 文化中国 >> 文章中心 >> 文化前沿 >> 文化现象 >> 文章正文 |
|
|||||
| 「乌托邦化」的身体与城市──荒木经惟的摄影地/人志书写 | |||||
| 作者:颜忠贤 文章来源:《空间》第122期,1999.10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12-20 | |||||
|
摄影家是勘测、潜蹑、巡弋都市地狱的孤寂行者,以及「经过配备的」把城市当成一座极端情欲的风景的「窥淫癖」漫游者。 ——苏珊·宋妲(注一) 「我和一个名字叫做东京的女人在一个也叫东京的地方走着并常常地为她拍照」。「是的,东京就像一个女人的身体」 ——荒木经惟(注二) 壹、前言 荒木究竟是一个摄影家(苏珊宋妲式的城市情欲风景窥淫者),还是一个行动艺术家(翻转暴露自己私密日常生活为挑战公共领域的展览发表之美学形式玩弄者),或是日本后现代文化形式代言人、传统美学新精神的诠释者(在国际艺坛上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前锋者),这些说法已有更多关于性、暴力、死亡、欲望、潜意识种种当代的理论为其批注,并甚至以其为个别学说之焦点分析对象。因此,笔者并不尝试对荒木摄影作更完整的全面性讨论,也不期待在此短篇幅文字里讨论其作品在当代或东方(亚洲或其目前涉及广义的东亚、东南亚…)的定位,甚至,并未对其最具争议的涉及性的较异于常态的参与及再现方式提出分析。而仅就笔者较感兴趣而不时在荒木作品中较重要的「城市」与「身体」两个视觉母题作较多的着墨,并提出部分的相关理论回顾与其介入作品的系谱式分析。 此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份着重于「乌托邦」概念的提出及演变,并尝试将「乌托邦化」的论述从建筑或地理学式的空间延伸至历史学的(尤其是后现代理论式的史观移转)时间向度,进而连接到女性主义式的反省男性物化理想化女性裸体的身体向度。第二部分则将荒木的作品视为一种「城市与身体的乌托邦化地志」来解读。然后在他的作品中,分类出城市与身体关系的三种模型,讨论其摄影中所处理的身体和城市的关系是因果投射的,还是平行隐喻的,或是互相渗透互相纽结的拼组模式。从而,在此三种模型中分析其乌托邦化城市与女体的个别特征及其在美学形式上的不同试探。第三部分则着重于「台北」作为荒木的新作品对象的意义及在其「乌托邦化」的城市身体地志书写系谱位置,并连接至他的「上海」、「香港」、「曼谷」之东南亚城市系列作品关系的讨论。 贰、「乌托邦化」与乌托邦理论 「东京是不是一个巨大的坟场?(住在这个城里的)我们是真的还活着吗?」 ——荒木经惟(注三) 乌托邦(Utopia)这个字的意思原指一个虚构的地点,字义上它是指一种无处(nowhere),或说一种没有真实基地的地点。 但是,没有真实基地的观点应是相对的,一方面它表达一种杜撰的不存在的空间状态,但另一方面它却又是与社会中的真实空间有一种直接或倒转「模拟」之普遍关系的基地。事实上,由于这种虚构的「模拟」往往起源于对社会本身的不满,因此乌托邦的描述通常会以一种完美的形式来呈现社会或将社会倒转,或是藉由旅者所到达的另一个地理上隔绝且遥远的地方,来呈现某种没有缺陷的世界状态,在里头,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与冲突都被解决了。 在一五一六年出版的汤玛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一书中,他着重的是国家的理想形式及其政体与法律所建构的殖民版图,来作为一种文明社会的想象模型(注四)。这种以乌托邦再现的方式来唤醒英国本身的缺陷是极具启发性的,更重要的,他也同时提出了一种有国土形貌的地理概念想象,关于场域的命名、边界、统合、控制种种空间的题旨。 但在傅寇(Micheal Foucault)著名空间权力论述的观点里(注五),则对乌托邦的模型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讨论。他认为我们所居住的空间本身即是异质的,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吾人得以安置个体与事物的虚有(地点)中,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而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更绝对不能相互叠合。因此,傅寇将乌托邦的虚构地点与真实地点的对立关系推论成一种混合、交汇的空间经验。他称之为差异地学式的论证形式,并在其中进行对人在差异地点中因为缺席而凝视而重构自我的怀疑、中性化或倒转的此空间关连的方式推论。 事实上,傅寇的推论还有更多定义为差异地点(hoterotopia)式的类型分析,但在本文中,仅讨论其对「乌托邦」概念的开发:从一组空间的对立虚构的真实的关系进入一种异质共存互渗的网络系统,在其中,地点被系统化与复杂化的可能是源于空间「意识」的参与方式,而非空间「实体」的描述问题。这种乌托邦引发空间「意识」的参与方式在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的后现代理论中有了更多的着墨。 乌托邦是一种空间性的事物,在一个像后现代这样空间化的文化里,它的前进或将有一番柳暗花明,但是倘使后现代被非历史化,且将事物非历史化,如我在在此时所宣称的那样,那么我们就更难局部化那个将乌托邦冲动导向实际表现形式的连锁。乌托邦在1960年代经历了一次不寻常的复兴,倘使后现代主义是六十年代的替代品,以及其政治失败的补偿物,那么乌托邦问题似乎可以关键性地测验出我们还有多少能力可以去想象改变。(注六)。 詹明信在此将乌托邦的问题从「空间性」拓展成「时间性」的,而且以「后现代」为时空坐标,来回顾「乌托邦化」成一种「历史」的动机,或许其中部分的意图应是和前述汤玛斯?莫尔的政治理想的不满足是有关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乌托邦化」的思考(或他使用的「冲动」此字眼)都是可发展成一种更周延的拓展视野的企图,那就是「乌托邦」不再是一个前述的空间状态的旧地理名词,而转变成一种新的历史行动,甚至是对最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运动理想纪元(六十年代)的复兴,因此创造一种「时间性」的悼念而非「空间性」的乡愁。 「乌托邦」一词所暗示的对不可能实现理想的冲动在更多种不同领域中还有了更不同的说法。 在琳达?尼德(Lynda Nead)的女性主义的观点中。「乌托邦岛(汤玛斯?莫尔的)和女性身体的特殊乌托邦式再现之间有着显著的类似之处,虽然,将家乡或国家联想成女性的身体,是西方政治和文化论述里的常见借喻,但是,这里的模拟已经超过了寻常寓意。因为,在此西方传统里的女性裸体传统上扣连了从真实(具有无可避免之缺陷的个别身体)到理想(裸体)的转换过程,从对于未定形的肉体实体的感知转移到对统整与控制的确认。也就在这种变换形貌的过程,让裸体不只是政治文化上的抽象隐喻,却进而成为艺术作品的(乌托邦式的)完美主体。(注七) 琳达?尼德以乌托邦的观念来推论其所关心的女体再现的问题,因而将「身体」对等于「空间」而成为一种隐喻,并进一步讨论日常生活所缺乏广义的欲望对象(包含「地理的」与「肉体的」双重论述领域),她甚至在更多艺术作品(当然包含摄影)的引述与分析中讨论到女体形象作为「乌托邦化」的感觉再现,以秩序、对称、协调与冥想等方式,将女性封闭地可视化但却也因此脱离女性的性身体与女性性欲所组成的大陆。 在其所期待的建立一种非传统封闭化的流动女体观念中,她希望不受约制地提供另一种「乌托邦」:女性裸体的理想──结构、几何学、协调──让传统不健全的、无定形的实质(感觉式的)团块,内在与外在的身体边界崩解了,代之以差异的再现,让女体的投射得以脱离任何(既定)完美的美学。因此,藉由她的观点,本文中的乌托邦论述可以更进一步地从空间隐喻式的(包含政治、法律、社会理想)的地理学投射,进入历史隐喻式的(跨不同时代的失落与冲动),再引申至女体转喻式的(欲望主体与其投射的性欲肉身对象的典范化与挑战)种种层面,并在这些层面的交互诠释中去讨论荒木作品作为一种城市与身体的乌托邦化地志,其内在的虚构式的肉身与空间的「模拟」所源自于的不满与冲突,从而可以分析出他的作品在美学形式上的演变、其乌托邦化的内容、及所诠释主题内在参差互动之不同呈现方式。 参、三种「乌托邦化」的地/人志书写模型 荒木:在东京我让我自己被城市引诱,并狂野而不思索地拍照。 采访者:也就是说,一种摄影的无停歇的射精…… 荒木:没错,城市彷佛也真正地为我而狂野。(注八) 在荒木的作品中,身体和城市关系应可分为以下三种模型(注九)讨论,并以其不同关系模型,延伸其个别「乌托邦化」的影像书写类型的分析。 (一)身体是先于城市的,先于设计和建造城市的动机。城市为身体的产物或投射的观点。一种人道主义的,史学的人种学式的,因果性的关系。 这种关系里,身体或其主体性或其意图或其心灵是原因,城市是结果。从现代主义式的角度而言,荒木的最好的作品是在这一种模型中,如他著名也是成名的1971年的「Sentimental Journey」里自己出演的新婚夫妇以蜜月写就的旅行遭遇。一起因为爱情的出游、等车、睡觉、性交的身体是先于城市先于其前往移动停留的种种场景。因此身体赋予了场景意义,赋予城市某种特有观点和参与态度。而这种观点正是荒木作品中「乌托邦」的原型。 如他的「秋天的东京」(Tokyo Autumn)、「Tokyo Nostalgy」、「终战后」(Post-war Japan)、「Tokyo Lucky Hole」和更多他在里头成长经历终战后废墟感的东京影像,这些影像参与并实验式地填充在那有时无人有时有人的照片中的城市风景中,饱含了荒木的记忆所堆栈出来的乡愁与感伤。这些实验有的还包含他每天活动连续拍摄2212张遇到的女人成系列的叙述,和更多延伸出来相关肉体书写式的城市搜奇。也因为这些关于东京类似挽歌式的追悼,荒木才能呈现荒木自己对这个城市所拥有过的自己历史的「乌托邦」式的再现动力。 城市允诺身体一个「自然」的脉络与环境。也因此同时是身体及其意识作用的地点,这种因果关系相对于荒木沉迷的「私─摄影」创作态度而言,是较贴切其回忆中遭遇城市的心智状态与运作方式,因而让观众可以更清楚地感觉到一种独有的忧郁感,因为在「私─摄影」中,拍摄者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不是无辜的记录者,而是蓄意的肇事者。所以城市不再是身体遭遇的背景,而是身体遭遇的现场。荒木在这种模型中的作品也因此显得特别生猛有力,悲伤的特别悲伤,淫荡的特别淫荡,怀旧的也特别怀旧。 尤其,对于荒木这种从小在这个城的劳工阶级区域长大的小孩而言;他所经历的东京其实是他的身世的一部份,也是他身体的一部份。这不仅包含他在空间层面涉足于东京非主流非地标式的各形各色角落(日常生活的、住民的,甚至是次文化的、色情区的),也包含他在时间层面上成长过程所看到东京战后的演变(从银座到新宿、原宿、涩谷更多新城市中心的分布与转移,从全共斗运动世代的没落到新人类消费世代的来临种种……所营造出来的都市地景或感知经验的改变)都是荒木在这种模型的作品里最容易散发出来的动人之处。身体不再只是城市的原因,他的身世使他的身体的意识(对女体或对其摄影的感官起点)成为城市的原乡,也促成了对此「原乡」无止尽的乌托邦式的找寻行动。(二)身体和城市的关系是平行的或异质同形说式的。身体和城市被理解是类似的,相合的互补物。其中一方的特色、组织和特征会在另一方反映出来。这种关系是再现的,或说是隐喻的。因此,在这种关系模型中,荒木作品的「乌托邦化」是接近傅寇的差异地点式异质并存的模式。 在荒木的作品中,属于这种模型的,最显而易见的,是「Tokyo Nude」,以一张赤裸的女体照片与一张被其称为「朝向死亡的一个城市」的东京照片之并列来突显两者对等的平行关系,而且,两者之间互为隐喻的特征可以被视为是广义的赤裸:城市被拍成废墟、后巷或大多无人的街景(注十一),并以其来对比独自的没有衣着的女体。 相对于前种模型,这种身体与城市的关系是另一种荒木常用的方式,尤其在其编辑或排列或重组照片时,以及在写真集或作品集或美术馆陈列的方式,他都一再强调这种模拟的关系,并在这种模拟中营造出彷佛剥离自常态的某种失落感,好象一个失忆者,在找寻其回忆中的旧地景或旧情人。 另一系统作品是「空花」,并列对比的方式一方面是天空与花,另一方面是黑白与彩色,或说在摄影类型上的分类:是街景与静物,室外与室内,出外景或在棚内式的对比。但是,其内容的平行关系仍是荒木一贯的主题延伸:城市与身体。因为,天空其实是作为「城市」的仰视地景(有些照片还出现电线杆或树顶梢的城市场景之暗示),而花则是其类「女体」性器官式的凝视对象(在另一花阴系统中可见),空花系列其实可视为是这种「Tokyo Nude」手法之延续。 「男之颜面/人妻EROS」系列作品也延续了这种并列方式,但这个作品有两点是比较特别的,一是:男人的出现,而且是特写的、大多正面的脸作为主题,这在荒木作品中是少见的。另一是:人妻的角色设定,这是一种日本色情电影或写真集的类型转用,用以强化角色在叙事上的幻想效果。但是,在整个作品中,这种效果并不只是在视觉上而更多却是在故事性上的幻想延伸。因为,在这系列作品中,身体与城市的关系虽然仍是平行的,但却有了更多相互渗透的关系。 由于男人出现的地方都是在街上的,而且身体往往是西装比挺地正式(甚至到有点僵硬)的姿态,但女人却是出现在厨房、地板、客厅、床畔种种会唤起「家」的意象的空间角落,并且是衣衫不整的,半裸,甚至全裸。因此,身体和城市的关系不再是以「女体对场景」的简单模拟出现,而是以「男体在城中场景对女体在城中场景」、「正式服装对衣衫不整」、「客气微笑打招呼对情欲幻想表情」、「街上公共空间对家里私密空间」进行身体和城市其中一方的特征以此种差异地点式的相渗透效果,也因此可以在对方的形象幻想延伸里再现而突显其虚构式的叙事特质。 在这个作品中,若其并列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关系是真实的,则应被放入第三种模型之中,因为这种虚构的想象其为夫妻关系所建立起的「身体与空间」配对关系是植基于日本色情文化类型的乌托邦式脉络,而非真正记录片式的田野调查成因(不过这也绝非荒木所愿意使用的方式与态度)。但这种模型中的荒木作品仍然呈现了一种新的视觉效果,并发生于「拍摄现场」与「照片发表展场」的不同脉络并列的装置性之中。然而在这种吊诡的并置中,荒木作品里所呈现身体与城市平行关系是隐喻的,容易创造出异质对比的特殊效果,但却也容易因此陷入某种架空观者情感的状态而成为某重纯视觉模拟的形式操作。 这种身体与城市的「再现」模式,突显了另一种「乌托邦化」的状态,那就是「原乡」消失了,或不再是如第一种「因果式」模型那么直接而重要。在这种差异地点式的模拟效应中,编辑者的角色重于拍摄者,展出的效果考虑重于现场镜头的考虑,所有在城市中身体的流动欲望被一组新的关系(复制的、拼接的、重构的)所描绘,此关系的「基地」被缺席而凝视的混合方式所重呈为一个新的虚构地点,或视为一种乌托邦化模式。(三)身体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第一种的因果性的,也不是第二种的再现式的,而是一种各部份的组合或集合,可以跨越实体间的门槛,形成连结,机转,以及临时性的,经常是短暂结合成的次群体或微群体的关系,这种模型立基于身体和城市藉以彼此界定和建造的实际生产力之上,而且因此使荒木作品中城市和身体的乌托邦地志进入一种布什亚「类像」(Simulacra)式(注十二)的影像书写策略中。 这种类像式的影像书写作品,不是一种强调城市和身体的统一与整合的平行整体论,而却是一种基本上是解离的系统和相互纽结的系列,一系列不同的流动、能量、事件或实体、以及空间,在多少是暂时性的排列里被拼组在一起或区分开来。因为两者被拍摄被复制时,以身体与城市里的原版性已然消褪。 从这个角度而言,荒木近年来做了许多这种方面的尝试,1999的「A/乐园」系列作品应该是此类型的尝试,虽然,在照片安排上部分雷同于「Tokyo Nude」的一张风景一张人像的安排,但这系列的作品并不急于在视觉上突显女体的赤裸与城市对等的荒废空荡,而却为真实的场景更加入了一种虚构的情境。在白天却无人的街道、被忽视的巷道、媚俗的娱乐设施、墓碑多的新宿办公大楼,他试图在这些世纪末的东京场景中改变其过去的废墟形象而建构一种新的「乐园」的观点,以一些他宣称为「变形的自我」的玩具怪兽,Komodon、Godzilla、Saurus放入城市中的种种角落,从荒木家的后院花园(反应其妻死后的心理状态的自我的小小世界)到东京著名的西新宿、歌舞伎町、六本木诸地(城市的历险记的现场)(注十三),另外这些塑料恐龙也同时用不同的姿势或拥抱或旁观或缠绕于女体的身上(这次照片中的女人有的全裸、有的盛装、有着更多种样态动作与表情)。这些女人大多在室内,但有些还出现在城市的街上、屋顶、窗口。这样的安排跨越了前两种身体和城市的关系,而更进一步地找寻各部份的组合或集合的可能,有些是临时性的,解离的系统的偶然纽结(空街上的唯一生物塑料怪兽造成的荒谬感),有些则形成流动的事件与空间场景,女体和怪兽并置造成真人的/人造的,美女/怪物,人尺度/缩小玩具尺度种种有故事可能发生的暗示。以「怪兽/荒木/自我」重塑一个城市做为「私」乐园的意识状态与被女体用各种姿态携行拥抱的参与情境,从而整合出某种身体与城市新的互渗关系。 但这些情境与关系所突显的暗示是类像式的,复制的大量生产而没有本源的非生物取代了作者取代了人作为身体与城市感觉主体的根源,其它的影像参与者则只好共谋地演出其虚构的后现代式场景脚本。因此,这种乌托邦化的类型和前二种是不同的,整个后设的影像叙事模式变成是一种无怀旧深度的逆转式的「乌托邦」模型。 在另几个计算机作品系列中,荒木更尝试用摄影材质与技术上新的型式操作来突破其惯常大量拍摄的旧式相片影像呈显效果,例如:「拍立得」系列以拍立得特有的色泽、尺寸与质地来统合人体(男、女、外国本国、赤裸着装)与城市(日本本国、欧洲、室内室外、天空、静物),但也仅于此,其并列异质人地状态的效果呈显了更多类像式的无根源无意识深度的意图与隐喻关系。而「色情女」所采用在女体与街景的黑白照片上涂上色彩或「死情」中用色光创造出来的影像偏色基调,都像是一种实验性的尝试,并未对其长期怪兽作品中的身体与城市的互渗关系做更进一步的发展,而却是进入一种詹明信式的无历史感式的怀旧,一种影像后制效果重于摄影原始照片文本更重于摄影对象根源性的作品类型:一种「乌托邦化」的虚构是没有本源仿真理想对象的虚构模式。 肆、「台北」及其它:「乌托邦化」书写地/人志的延伸 台北现在拥有的一些感觉是东京已然消失的欲望与活力。 ——荒木经惟(注十四) 「台北」在詹明信评论「恐怖份子」的一篇文章中是如此被描述着:(注十五) 「台北在此处被描绘出的轮廓是一系列附加的盒子般的居住空间,身处其中的角色都被某些方式限制住了。电影告知我们台北和传统及大陆上的现代中国城市以及台北的文化和历史风格与其它东亚城市之不同。」 「台北的面貌与侯孝贤的台湾乡野的意象有极大的差异。一个外国人和外来者或许可以将这观看都市经验的方式连接到这小岛的「总体性之再现」,认为这岛屿同样是个「非国家的国家」。各式各样宽广不一的封闭空间描绘并具体表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衡,不公平现象。」 詹明信在这篇文章的推论中小心地避开书写第三世界国家城市极容易陷入的三种窠臼:(一)一种落后的乡野的刻板印象(二)另一种古老国家传统的空间遗址(三)现代化或开发中国家的不健全城市状态。并进而提醒了「台北」在特殊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如何被较准确地描绘,而不只是作为笼统的开发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国的首都而简化地定义。 在荒木另一系列的以东南亚国家主要城市摄影的作品中,「台北」和其它的「上海」、「香港」、「曼谷」有何异同?或是以一个外来的摄影者的角度如何留意詹明信提醒的这些窠臼?甚至,这系列的作品所延伸前述三种身体与城市模型与其「乌托邦化」的想象究竟为何? 虽然,荒木在形式上作了部份新的类装置化的尝试(其实是延伸其在日本将大型照片装置于城市角落再拍成照片形成两者异质并存的视觉效果之处理手法):如在曼谷将「花」的摄影作品放入河中再和船、河岸、皇宫并列成画面中的主景,如在上海的巷弄将「花」的彩色照片放在墙上,并拍下与巷中的晾晒衣物、电线及水管甚至是路过住民的场景。但是,荒木以这些城市为拍摄对象并没有任何预设的创作立场,或是刻意避开的视觉主题,因此,他依其原有的摄影态度与方式,来进行与这些东南亚国家没有深入探究企划而着重印象经验式的影像对话。 如此,他的这一系列作品,包括台北,都极容易被指控为「(一)荒木对台北女人的物化凝视,仍然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体制下,女体的再现因男性的观视而物化扭曲。(二)柔弱梦幻的沙龙美感是殖民者对于被殖民者异国情调的情欲想象。(三)日本观光客为台湾色情行业主要顾客的历史经验的指涉。(四)日本色情写真集、录像带跨国商品在台湾漫延的更进一步支配。」(注十六) 但在本文中所关切的,却是这些荒木「偏见」背后所透露出来其「乌托邦化」城市与身体的创作倾向已然扩大从日本(自己的原乡)转移到外地(他者的城市)。这种空间的版图扩大在「乌托邦化」的行动上有两种值得注意的脉络:一是旅行本身所容易藉由地理上遥远且隔绝的「他方」美好想象来呈现追念自己的缺陷。(荒木曾表示台北拥有某种东京已然消失的城市的欲望与活力),二是东南亚正是过去大东亚共荣圈的版图,殖民地往往是殖民者以乌托邦再现的典型基地。这些城市的被拍摄方式不时呈显出过去历史脉络上的重要地理联系。 但是,荒木在处理这一系列的作品中,并没有对身体与城市的关系提出更进一步的发展,他在「乌托邦化」这些异国的被日本殖民过的城市时大多仍重复着过去作品中既有现场纪实式的手法。「台北」并没有特殊的不同。在这些作品中,虽不至于出现「风景明信片」式的地标景像,但更多的画面,仍只停留于观光客式的猎艳搜奇基调,许多浮光掠影式的瞬时遭遇,拍摄女性裸体的部份和拍摄城中摩天楼的部分都像是「到此一游」式留下荒木签名的一贯手法。 不论荒木表示对台北街头摩托车肌肤相亲紧密拥坐的男女特别感到有趣而认为是猥亵行为的公开展现与日常生活化,或是宣称槟榔西施在透明玻璃门内呈现其欲望的视觉效果甚于在密室中的裸体,然而,相较于他在东京一系列题材雷同的作品,会发现其对城市与身体的乌托邦化想象所呈现的强度是难以比拟的。因为从第一种模型的角度而言,荒木在城市与身体的原乡皆在新宿在歌舞伎町,在自己的妻子与情人,那种因时空过往而引发的失落与激情是其乌托邦式的摄影风格里真正力量的源泉。而到了观光的异国异地,这种力量显然削弱许多,甚至仅是沿袭或重复着其过去的热情。 荒木在这系列中所建立的身体与城市的乌托邦化地志书写应是被放在第一种模型中讨论,虽然,他也尝试制作「荒木映画」(Arakinema)一种多媒体式的写真音乐录像带的放映方式(或是像「色情女」上涂抹颜色的照片后制操作),但这些无论是摄影装置或异质并置的第二种模型式的或「影像后制」式第三种模型中类像化式的尝试,都呈显了一种荒木在面对其「乌托邦化」新主题上的焦虑,与找寻更新表意形式与之对应的苦恼。 伍、结论 在红磨坊里,我们看见另一种驱魔的暗示,也许是典型法国式的脱衣舞,事实上并不是抹杀色情,而是「驯服」它。 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注十七) 荒木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色情」特质是看起来最不被驯服的。但他的整个作品系谱却是源自最驯服的日本色情工业脉络之中(甚至荒木自己也曾投身于这个工业之中扮演消费体制里的角色),因此,他的「不驯服」应被放入更广义的女体消费策略中考量。(例如:他所拍摄的女性多为美女且姿态上的考虑也是以挑逗吸引男性观点为前提的,因此他不会拍摄到逾越女性边界的物质:如母奶、眼泪、尿液、经血式的女性主义创作者最关心的主题)。 这种「驯服」的疑旨放入本文中「乌托邦化」的课题之中,所呈现的同步反省是:荒木的身体与城市经验其实是现代主义式的,一种强调「私」的摄影观所呈显的感觉结构式的参与方式,甚至着重于有根源有地着感的和人及城市的意识状态有着现象学式的「原乡」找寻的无止尽冲动所构成其作品强烈的风格。 这种「原乡找寻(找寻其被驯服的意识起点)」式的作品的主题内容风格呈现在其「乌托邦化」的第一种模型中是最贴切的也最能符合其型式上的美学企图,但在第二种与第三种较接近后现代主义式的「异质拼接组构」或「无根源再现」的美学型式操作中,则突显出一种更深层矛盾,一种只在再现物中出现的奇观,一种意象,其描述的主体(某时代的意识及其参与的「身体城市」的奇遇),不论再怎么狂野,再怎么惊人耸动,都不再存在,或是无法再以等量狂野耸动的美学型式「再现」它(或仅是与它「对话」)。 而更矛盾的是,这个奇观正发生在荒木得到最多全世界注目的现在,与他来到「台北」自信满满地相信在此他正发现自己那个已然失去而不断怀旧的城市(东京)与里头回忆中美好身体(妻子、情人、美少女……)的替代者,一个替代的「乌托邦」。 「台北」因此是荒木经惟「乌托邦化」摄影地/人志书写一个理想的终点(或说落点)与反省的起点。 注一:出自苏珊?宋妲的《论摄影》黄翰荻译,唐山出版社出版。 注二:出自伊藤俊治Toshiharu Ito, The Unconscious of Tokyo, Forum Stadtpark, Graz, 1992。 注三:出处同注二,此文为诸多讨论荒木的文章中较仔细地提及东京作为其作品脉络的内在关系,包括对东京现代化与以西方认识论模型重塑东京形象在日本摄影中的困境有多方的推论,并因而推崇荒木作品中再现的「女人/东京」与「无多的东京性(Tokyoites)」所创造了的一种此城市特殊潜意识式的流动意象。 注四:出自汤玛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志文出版社 注五:出自Michel Foucault "Texts, Contexts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 (1), (Spring): 第22至27页。 注六:出自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吴美真译,时报出版社,第9页。 注七:出自Lynda Nead(1992), "Framing and Freeing: Utopias of the Female Body" Radical Philosophy 60(Spring),第12至15页。王志弘译,收于:性别、身体与文化译文选,第81至92页。 注八:出自 Nobuyoshi Araki Interview with Roland HagenBerg/Walter Vogl,收于1994年荒木在威尼斯展览的作品集中附录第183页。 注九:这三种身体和城市的模型是从Elizabth Grosz(1992)"Bodies-Cities" in Beatriz Comina (ed.), Sexuality & Spa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Architertuda Press, 第241至253页中延伸出来的,Grosz在文中提出这三种模型是用以讨论身体政治与政治的身体(Body Political and Political Bodies)时身体作为社会建构的类型化说法,并进而分析城市的形式,结构和规范渗入且影响了构成肉体和主体性的要求,且在此文中并未进一步地分析这种主体性和空间的排列连结关系,仅转向乌托邦的类型延伸说法,来连接对荒木作品分析的论述。 注十:出自东京都现代美术馆研究员石田哲朗 (Tetsuro Ishida, Curator,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Tokyo)摄影能让人幸福吗?(Can Photography Make Someone Happy?)第70页。 注十一:出处同注十。 注十二:Jean Baudrillard(1983)Simulation,New York Semiotext(e)。这里引用布什亚的类像理论观点并没有更深入地讨论其内爆的超真实性(hypereality)问题而只是以其没有指涉根源的类像为一种相对于其前两种乌托邦的概念模型。 注十三:出处同注十。 注十四:荒木经惟于七月二十八日再度来台湾拍摄作品时记者会上所说的话。 注十五:出自詹明信〈重绘台北新图象〉,冯淑贞译,收于《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一书,第233至275页。 注十六:出自张美陵〈荒木欲望的台北女体〉,刊于《现代美术》,第80期,1998年11月,第43至54页。 注十七:出自罗兰巴特《神话学》桂冠出版社,第131页至134页。 |
|||||
| 文章录入:古言月 责任编辑:古言月 | |||||
|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
| 最新热点 | 最新推荐 | 相关文章 | ||
| 没有相关文章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管理登录 | | |
 |
粤ICP备05083455号 Copyright 2004-2005 CulChina.Net 主办:深圳大学文学院·传媒与文化研究中心 站长:孙海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