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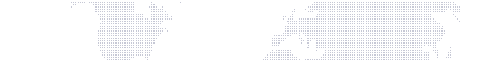
| | 网站首页 | 文章中心 | 学术动态 | 资料下载 | 建议留言 | 文化论坛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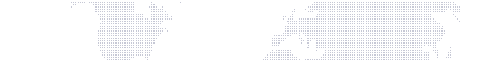 |
| 您现在的位置: 文化中国 >> 文章中心 >> 媒介研究 >> 电脑网络 >> 文章正文 |
|
|||||
| 无言的焦虑 | |||||
| 作者:不详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12-19 | |||||
|
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描述麻省理工学院黑客文化的《第二个自我》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
每年春天,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都要举行一场奇异的比赛,它的形式像选美,但比赛的目的却是评出“校园里最丑陋的人”。比赛往往持续数周,那些认为自己奇丑无比的学生在学校的主要通道上游行,炫耀自己脸上的疽疹、罗圈腿以及豆芽菜般的体型,到处拉选票。观众们一本正经地进行投票。
30年前发起这一比赛的学生现在已是一所大学的教授,他为自己对学校文化的贡献感到骄做。“人人都认为工程师丑陋。如果你在哈佛读书,别人会把你当作绅士,身边有无数的追求者;但进了麻省理工学院,你就好比一头怪物,一件工具,一个没有身体的人。选丑比赛是在讽刺最明显的事情。”
今天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把比赛看作一个仪式,一个否定自己身体的仪式,对这样的仪式感到自在;但与此同时,一些人的内心又很不平静。“比赛大一针见血了。我还没有丑到有资格参加比赛的份上,但也没有漂亮到足以做一个正常人,能够找到女朋友,并且知道在舞会上干些什么。”“我恨这样的比赛。它败坏了整个学校的名声,让我觉得丢脸。”虽然整个过程很像是一场玩笑,但确实道出了某些真情。学生们是在表达这样的认识:在外人的眼里,工程师是丑陋的,缺乏七情六欲。
不用说,许多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为自己的身体而骄做,但校园里的确普遍存在一种厌恶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并不是个人而是社会疾病的一种症状,社会把人划分为两类:一类善于同物体打交道,一类善于同人打交道,它不仅承认而且有意加深了这两类人之间的鸿沟。 这一做法的代价很大,最明显地体现在孩子、尤其是有天份的孩子身上。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自述说:
“我一向觉得自己既丑陋又无能。学校里所有的男孩都有朋友,擅长运动,对学习满不在乎。只有我总是一个人鼓捣无线电。后来我发现了一些和我有同样爱好的男孩,他们也都不合群。所以,当我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看到一群一群的孤独的学生埋头子数学和科研。把自己看作失败者。举行进丑比赛时,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像他这样的学生最终会适应环境,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找到自己的社会归属,但这一过程将不会很容易。那些参加选丑比赛的人实际上是在说:“我们是丑人。你们可以保持你们虚伪和冠冕堂皇的价值观,以及你们的成就感。我们比你们更好、更纯粹。”
丑陋文化也存在等级。在麻省理工学院,一些学科比另外一些学科更丑陋。一些自我中心主义者比其他同类走得更远。而计算机系的学生就是这种“放逐者中的放逐者”。他们感到机器把自己同他人隔绝开来,他们是“另类”,是技术呆子,是孤独的人和失败者。在学校的计算机系统上,user(用户)被称为“luser”(与“失败者”发音相似)。由此,麻省理工学院成为黑客的原产地。
这些黑客们把自己看作艺术大师,追求过程中的快乐而非最后的结果。人们已习惯于接受那些把玩画笔或凿子的艺术家,他们中很多人对最后的成品并不在意。但是,当一个工程师对他的工具采取类似态度时,人们恐惧地将其称为“精神手淫”。工具是造出来供人使用而不是把玩的。它们属于工作的世界,而不是个人的世界。看到黑客对机器如此亲近,人们难免在心里感到害怕。这种害怕是多方面的。有人担心年轻人会像吸毒一样对计算机上痛,自绝于社会,将生活的意义狭窄化;还有人则担心“黑客心理”的扩散,这种心理被描述成不健康的:宁愿与机器而不是与人呆在一起。
事实上,黑客生活在矛盾之中:这群“失败者”同时又以“精英”自居。他们是深奥的知识的拥有者,是计算的纯粹性的捍卫者,在他们看来,计算不是一种手段,而是具有内在的审美价值。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黑客说:“黑客活动充满男子气概。你可以看到你能把自己的头脑和身体推进到多远……黑客多少带有自我毁灭的念头。女人不是这样,她们考虑问题更平衡。”黑客与计算机的伙伴关系,对于那些寻求逃避人群的青少年来说,具有诱人堕落的魔力。
一位每天在计算机前度过15个小时的黑客说:“从外表看,好像我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生活。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首先,有其他的黑客伙伴,我们一起谈论系统。其次,我把大量时间花在电子邮件上。在送出邮件时,我觉得我和机器找到了心灵感应。”很多黑客都曾痛苦地发现,自己和其他人格格不入。这种发现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刻骨铭心。现在,他们第一次有了归属。
黑客并不是仅仅同计算机一起生活;他们生活在围绕计算机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中。黑客文化是一种孤独者永远不会孤独的文化。黑客对任何“真实世界”感觉奇怪的东西都能够容忍,对“真实世界”的评价却不是很高。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害怕现实世界的复杂关系,也许是因为曾被这样的关系深深伤害过。
一位黑客说:“黑客活动既简单、又安全。如果被人拒绝能够引发痛苦的话,在黑客世界里,不会有被拒绝的危险。在计算机上你清楚一切情况,知道每件事都会有结果,所以你对自己充满信心。而在社会上,你还必须自信别人都会对你好。别人对你的反应是无法控制的。在计算机上你却拥有完全的控制权,谁也不能影响你。”
简单他讲,黑客活动比约会女朋友具有更多的确定性。机器的想法是不变的,而别人的想法则是常变的。为什么人们不像机器一佯做事?这样的逻辑推理令正常人毛骨惊然。
我们被机器所包围,我们对它们须臾难离,我们为它们变得如此强有力而不安。核机器已拥有摧毁整个地球的能力,而电脑这种“心理机器”又会把人类引向何方?黑客与机器间的亲密关系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机器对黑客的控制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也感受到同样的控制。黑客想要变成某种“装置”的想法令人恐惧,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同样的想法。黑客把机器当作一个安全伙伴的行为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也经不起同样的诱惑。
对机器的亲密认同引发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无言的焦虑:机器是仍然在服务于人类还是已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更关键的是,机器是否已开始为自身的目的而工作,而这一目的是人类一无所知、也无法控制的?
如果社会对黑客过分认同于机器感到焦虑的话,也许关注点应该集中在产生黑客的社会和心理根源上。为什么有些个人只能从与机器的交互而不是从社会交往中获得满足感?因为当今社会弥漫着一种“人人为自己”的气氛。学校、政府和媒介都在鼓励人们追求成功、地位和金钱。没有人提到人类的相互依赖性、共同的事业和社会归属感。技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崇拜。整个社会都以目标和任务为中心,许多人把生活全部放在工作上,没有时间顾及他人甚至自己的家庭。个人实现成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团体感和对他人的关心荡然无存。在这样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里,黑客不过是一个缩影。
另一方面,这样的认识也不应该把我们导向一个误区,即把黑客看成病态的一群。这对黑客是不够公平的,因为将其等同于“瘾君子”,可能会使我们的心目中产生一个头脑麻木的患者的形象,而忘记了黑客活动中具有创造力的激动人心的一面。也许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也许只有具备多种多样的性格的社会才是健康的。我们既需要外向开拓的人,也需要内向思辩的人,需要思想家也需要行动家。从许多大科学家的经历也可看出:羞于与人交往的孤独者常常会创造惊人的构想和发明。今日的青少年黑客是未来的栋梁之材吗?多给一些时间,也许他们会的。 |
|||||
| 文章录入:古言月 责任编辑:古言月 | |||||
|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
| 最新热点 | 最新推荐 | 相关文章 | ||
| 没有相关文章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管理登录 | | |
 |
粤ICP备05083455号 Copyright 2004-2005 CulChina.Net 主办:深圳大学文学院·传媒与文化研究中心 站长:孙海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