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11月至2001年1月,笔者所在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斯马特博物馆举办了题为"取消:在中国展出实验艺术"的中国艺术展。如这次展览的组织者巫鸿教授所称,
这次展览的主题并非艺术家个人或某一艺术群体,而是一次"由于被撤消"而从未实现的展出。[2]换而言之,这是一次关于展览的展览,更准确地说来,它关切于当下中国实验(先锋)艺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下生存并展现其自身的问题。这样的思考确乎切中要害,因为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实验艺术的语境问题远远重要于它的风格与语词,正是前者决定了后者的基本面貌。
独立电影人吴文光由于拍摄并制作了关于这次被取消的艺术展的记录短片而介入了这次芝加哥展览。同时,借这次展览的机缘,吴文光在芝加哥大学电影研究中心放映了他的新片《江湖》。这是在芝加哥大学第一次以如此的规模公开放映他的作品,[3]也是一次绝好的了解中国先锋电影在美国的接受状况的契机。笔者在参加这次展览有关活动,访谈了一系列对中国电影有兴趣的有关人士之后所写成的这篇观后记,希望对我们的"反身自察"能够有所裨益。
1.背景与前景
在吴文光的影片反映之前,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先锋电影一无所知, 但或多或少都曾接触或耳闻过以商业片面目出现的中国"大片"。
在芝大所在的海德公园最大的食品超市的录像出租部,我们可以找到诸如《摇呀摇,摇到外婆桥》(英文名"上海三重奏")、《炮打双灯》(英文名"红炮仗绿炮仗")这样出自"第五代"导演之手的"中国经典",陈冲导演的《秀秀》(英文名"天浴")虽然不属于"第五代"及中国大陆电影范畴,却由于其演绎"中国形象"的策略上与第五代有意无意的共谋之处,自然而然地被调查者理解为中国影片。末代皇宫,西部荒原和半殖民地都会上海这样典型的"中国情境"在美国大众中之深入人心,即便成天被教育反"程式化"的学院知识分子也未能幸免。一部被调查者提及的美国影片《红提琴》,以时空交错的视角述及一把17世纪制作的小提琴,饱经沧桑流落各地的故事,其故事情节和中国并无必然联系,但对于西方观众而言,中国部分"文化大革命"的故事与影片那精致的怀旧情调却非常合题,通过对历史影像的复制和抽去其历史内涵的表述,东、西方达到了某种惊人的一致。这种带有强烈倾向性的"误读"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第五代"电影的海外接受多少和西方本土文化思潮的联系。
吴文光的影片,尤其是《我的红卫兵时代》,最早也是以这样的姿态进入西方视野。尽管《我的红卫兵时代》包容了当事人集体记忆的重写,具有某种互动的意味,但是,它在西方的接受多少得益于一个为西方人所熟知和期待的历史潜影(文革)。而《江湖》则不同。《流浪北京》尚且使用了一个对于西方人来说不陌生的意念,那便是做梦者的形象,从吴文光亦步亦趋构造北京版流浪艺术家神话的方式来看,纽约东村到圆明园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般遥远。然而,在《江湖》一片中,最后的光环也被卸去了,生活的原生态所展现的不是最后的梦想,而是一群任何意义上都疏离于"艺术"的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实况,如怀斯曼,吴文光所心仪的美国大师[4]所言,是普通人的"庸常、激情与欲望"。很显然,在他刻意强调的《江湖》的记录特性后,吴文光使用了一类不同于从前的叙事策略,但在我看来其最终结果并没有暗示着中国电影在西方世界的接受格局的一种新的前景。虽然由于,在中国观众中间,吴文光的纪录片往往意味着一种更独立于传统电影的叙事性的真实性,乃至于一种生活的常态,我的美国同学普遍反映,在他们看来,吴文光的影片可以被划到他们称为"先锋电影"的范畴中去,理由是这部片子里有着许多可以辨识的叙事意图和非常态,对他们而言这部影片更接近于纪录
戏剧(Doc drama)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
2.精致与粗糙
和另一位记录电影导演张元相比,吴文光对于技术的把握显得更加细腻全面。这种感觉印证在《江湖》这样一部表面显得异常粗糙质感的纪录片中。乍看起来,这是一部被还原到最原始状态的生活的实录,一个再庸常不过的主题。一个来自河南农村,名叫"远大"的业余演出班子,在北京进行"卫生检查"时被轰出了这个城市。班主老刘有事回了老家,他的儿子小刘接手这个摊子,在百无聊赖地等待"检查"结束时,发生了一系列的琐碎事件,在北京郊县的零星演出,一些"演员"的离去,小刘的朋友从广州来了,
昨天的哥们突然耍了一个小阴谋,又消失得无影无综......这里没有严格意义的戏剧化事件,有的只是一些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情节",这些情节如果还对影片构成意义,那么就是它们本身没有太多意义
:炎炎的夏日里,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城市郊外的垃圾场边,无聊地推搡着、追打着,消磨着时光,象怀斯曼所提示的那样,这里富有趣味的就是生活的庸常和盲目。吴文光声称他在这部影片中力图表现生活自身而不是编排它,在技术上就是他避免从一个摄像者的地位与被摄者交流,在工作时,他的数字式便携录像机大多数时候是放在腰部的位置,而不是举在头边(但这并不妨碍他注视取景器进行构图)。
但是透过"汗味、人的呼吸和心跳"(吴文光语),这部影片远不象我们第一眼印象中的那样松散与粗糙。我猜测,吴文光并不是总是象他所称的那样不通过取景器构图,事实上,大多数镜头不仅考虑了构图问题,而且拍得相当平稳。看上去,吴文光对拍摄主题的选择也是很有想法的,因为这群"流浪艺人"为一种不受干扰的拍摄提供了最大的可能,被拍摄对象很容易维持在他们的"自然"状态中,某些小小的"即兴表演",恰恰是他们即将被构造出的"原生态生活"中最需要的一部分。为我的观点提供支持的最重要论据是吴文光本人所流露出的创作理念,在他称为"在路上"的这种生活状态中,他说他看到了与80年代的社会转型期所迥然不同的一种东西,一种反方向运动,如影片中形象化地表现出的那样,装载着演出队的大篷车是背向观众远离我们,而不是摄影者占据大篷车,形成一种永远"向前看"的视觉运动。在笔者看来,这种和纪录片自身视觉特性结合得如此紧密的理念不大可能是即兴的发挥,而很有可能是一种精心的编排。
3.演出与观众
对于观众对他的作品中所可能含有的隐喻及其阐释的质询,吴文光表现出一种否定和回避的总体态度。例如那顶贯穿影片的活动大棚,是演出班子的戏台,也是全体人吃喝拉撒的生活空间,当它一次次地在片中被支起又放下,摄影机总会长久地对准它并让它布满画面,破烂的布片的缝隙间只能看到几线天空,这样压抑的场景,用芝加哥大学电影研究中心教授汤姆·坎宁的话来说,这样一个"幽闭空间[catastrophic
space]",是否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或是否是一个戏剧性的背景?对这样的质询,吴文光的答案是否定的。
他力图向人们证明,这样的生活不是对于生活的某种解释,而恰恰是生活本身。例如,支起大棚的段落无非只是在暗示着地点的变化和又一段漫游生涯的开始。可是,
大棚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是一个舞台,有它实际的道具作用。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影片所构造的世界中它都是一个封闭的、表演的场所,无论有意或无意,另一种意义的演出正在被唤起,对于局中人,
演出只是他们日常经验的某一部分。可是恰恰是摄像镜头的存在,而不是它的消失,把整个生活重构成了戏剧。这种戏剧化首先不是因为有了表演者,
而是因为有了一个沉默的,在摄像镜头后的观众。镜头的作用在我看来就象一个榫子,结结实实地插在那原本均质而透明的生活中,使得它出现了一道微妙的裂痕。
面对俗世众生,《江湖》依然掩饰不住地流露出一丝居高临下的悲悯情怀。只不过由于拍摄者表面上对于优势机位的放弃,这种悲悯包裹了一层中国式的世故。片中有一个"促膝谈心"的场面恐怕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拍摄者、被摄者和摄像机看上去在一种平等的三角形关系中,
被拍摄者, 那个跟着班主从农村来讨生活的年轻人,故作世故地向拍摄者讲述着他的"处世经验"
:"你说我他妈的能相信谁?人心隔着肚皮,这世界上就是谁也不能相信。"(大意如此)拍摄者的对答从剪辑中被去掉了,我们看到的是一幕独自演出。它用如此轻松、平静却没有反馈的方式被展现出来,
使得这一幕的视觉真实充满了空洞的意味。
相形之下,
远大歌舞团在现实中的真正观众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他们成为《江湖》中的零余者,镜头常常越过他们的头顶,而直达舞台中央。作为中景的这些观众成了舞台的一部分。在片中的仅有的几个面向他们的场面之一是一个近距离的摇镜头,那缓缓切入的,一瞬间喧闹的声响、斑驳的背景都从情境中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人物扭曲的、古怪莫名的面孔。[5]拍摄者的机位虽然并不占据优势,这情境却因镜头中一丝调侃的意味而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疏离出来,为这些庸常的段落注入了超越的诗意。
4.语源与读解
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还有片中不动声色地援引各种语源,并把它们通过视觉形象衔接在一起的方式,令一个远离精英社会的边缘空间也充满了语义的张力。从八十年代流行音乐中的"经典"说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到九十年代的(北京迎接国庆前的)"城市卫生大检查",到皱巴巴的购物袋上的张曼玉,一个西方观者通常会忽略这些细节的涵义,但对一个中国人,即便是象我这样离开中国已经两年的中国人,也强烈地起到一种提示中国既有的那种生活经验的作用,用吴文光自己的话,使你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俗世记忆中的"温暖"。同时,使用无线电话的班主堆满皱纹的侧脸后闪现出的天安门广场的远景,穿警服的公安人员和字幕中不断闪现的"北京","十月一日",又往往向西方人暗示着某些他们耳熟能详的语源。这两种不同的援用语源的方式虽然令《江湖》对于中国或是西方的观众都可堪接受,它们在片中的共存也使得这部片子的叙事带有了某种程度的含混性。
"江湖"这题目本身是一个打造出的语词,并不代表着实际生活的场景或空间,它语义的模糊也同
暗示着影片叙事的含混。虽然吴文光坚持认为《江湖》是一个既得于民间的意念,这个意念却并不真正是源自他的被拍摄者[6],事实上,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这些人从未看到片子最终的剪辑结果。芝加哥大学的美术史教授詹妮对此所提出的问题非常具有针对性和启发性,如她所言,"江湖"本是一个指涉民间的概念,然而这部片子预设和最终的观众是中国的、西方的知识分子。在哈佛大学,"江湖"的语义比在别的任何地方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一个角度这似乎可以证明,在今天的大众话语中,无论是金庸、仙剑奇侠传(一部经典的武侠游戏),江湖都是一个虚拟的场景,一个意义不甚明确的符号,进而,只有在知识分子的阅读与重新书写中,"江湖"的语义才最终超越了它的口语属性,成为生活真实的戏仿,一个优美的、对于平庸的并不平凡的表述。
5.摄者与被摄
吴文光多次向他的听众提到,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事实上也是他和这个团体共同生活的过程。在拍摄伊始,他依然感受到自己作为拍摄者的地位,然而随着拍摄的展开,这种优势的地位消失了,
最终的结果是他自己也不再能区别他与被拍摄者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他已经变成了这个团体的一部分。这种解释显然不能涵盖吴文光和被拍摄者的真实关系,因为摄影机的机位并不是支配这种关系的唯一因素,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促膝谈心"段落中,摄影机的位置的确被巧妙地掩藏起来了。按照吴文光的解释,当摄像机只是象一个物品一样被置于腰间,摄像者不再用他的眼睛透过镜头,充当一个富有权威的支配者时,摄像机位已经不再对被拍摄者构成优势了,久而久之,对于习惯了这一幕的被拍摄者来说,它看上去也就象大棚里一个花一块钱买来的塑料漱口杯那样普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摄影者赋予摄像机的权威地位就从此消失了,相反,一台一千美元的DV数码摄像机,无论是放在什么地方,对一个身上只有"一块多钱"(片中人语)的农村年轻人,无论他是否真正清楚它的价格,不难想象都依然有着魔咒般的力量,足以激发起一种远远谈不上平等的敬畏感。进而,恰恰是现在,这种经过修正的人与机器、拍摄与被摄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最有权威的并不是摄影者,而是那台摄像机,以及摄像机镜头后潜在的观众,而摄像者放弃了支配性的机位,同时也放弃了引导叙事的责任,成为一个沉默的游离于他们之间的旁观者,从而也使得这个段落中有了一种微妙的、甚至谄媚的表演气氛。
6.真实与幻象
前面提到,吴文光是作为展览"取消"所邀请的艺术家来到芝加哥大学的。吴文光不仅介入了"取消"和它所基于的中国展览,而且也和艺术家宋冬合作,拍摄这个"关于展览的展览"。在这次展览中和其它一系列展览中,
宋冬多次地使用和引用他近年的作品中常常出现的一种手段,他先拍摄一系列的录像片断,然后把这些片断投射到另一些物品、影像甚至是镜面上。通过变化这些"屏幕"的环境、材质和运动,他的作品产生出了某种奇异甚至是奇幻的效果。例如,有一件作品是将拍摄艺术家的一只手在空中"抚摸"的录像片断投射到艺术家父亲的脸上,看上去似乎真的有一只手在那里温情(或恶意)地抚摸。然而,被抚摸者是不能意识到和观察到这一幕的,即便他注视投影仪的方向,那里也只有一片光亮而已。
从宋冬的这些作品的意念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足以图释《江湖》在美国放映所激起反应的寓言。这实际上就是关于电影本性的那个(柏拉图)山洞寓言,只是现在山洞已经消失,消失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投影被移到了一个展览空间中,而是因为通过把幻象和它的生活原型并置,生活本身已经和幻象难分彼此。艺术家之所以可以做到这种并置,或许就是因为,当视觉图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现实时,图象在前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那种魔力已趋于消失,它对被拍摄者(投影者)已不足以构成一种令人惊悚的力量,比如,在如今的公共空间里,一台摄像机(投影机)的存在并不比一张法院的公告便具有威力。但是,被摄者与拍摄者之间的那种难以言述的疏离、对立的关系并没有由此而消失。相反,由于摄影者(投影者)拥有了远远优于被拍摄者乃至观众的物质资源优势(象昂贵的摄像、摄影设备)和空间优势,他们的关系是远远不够平等的。
关于此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另一个"抚摸"系列的录像展览现场,那只录像里在空中抚摸的手戏谑地调侃一些在场的观众(包括一些年轻女性)。在一个合法的展览空间里,艺术家可以随意选择他"抚摸"的对象,而任何自愿进入此既定的展览空间的被"抚摸"对象都被期待着有一个平静的、不必大惊小怪的反应。另外一方面,从阐释权力的角度来看,从拍摄的伊始,被拍摄者就已经注定处于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地位,他们的形象被剪辑,不露痕迹地调侃与编排为非真实的影像,而当这种影像又以真实的名义投射回真实时,被再次利用为作为投射屏幕的被拍摄者(被投影者)却无法意识他们身份的尴尬,他们甚至也永远没有站在摄影机(投影机)另一头回观的可能。■
前不久看了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乍想起来,《江湖》与这部影片似乎相去甚远。但是。某种意义上,它们却"异曲同工"。这两部影片展现的空间都接近于乌托邦,又都有不完全是乌托邦空间:两者共有着某种"超现实"的抒情意味,都是现实与乌托邦空间的混和。比如,《我的父亲母亲》语涉的是一个"不可能的过去",一个近乎世外桃源的乡村聚落,而《江湖》记述的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特殊人群,一种现实生活的非常态。但是,张艺谋的影像制作又是极尽现实主义的,一如他从前的制作,现实场景的设置融汇了绘画、摄影、音乐甚至于时装领域内对"中国身份"的表述的精华,[7]而《江湖》干脆被艺术家指认为生活本身。同时,在这两种"现实主义"的背后,《我的父亲母亲》里我们看到了90年代那个被认为已经死亡的文化英雄的悲天悯人,而《江湖》则是化大俗为空无高妙的文人趣味。在米歇尔·福柯的表述中,无论是张艺谋的东北农村田园还是吴文光的江湖戏班都是"另类空间"[other
place],一个疏离于日常生活真实却又栩栩如生的镜像世界。它本依赖于与真实的互为本文而存在,再现真实的欺骗性在此却掩没了电影纪录之笔所独备的震撼性与批判性:它本负载着太多的个人记忆,却变成了集体历史的切片,一条永远不可能进入、也不可能具有太多社会积极意义的遗忘之川。
注 释
[1] 本文引用和参考了一系列受访者、包括吴文 光本人的言论,他们中间有芝加哥大学的电影 研究专业研究生蔡柏贞、Jean
Ma、东亚专业研 究生包卫红、Bret Sutcliffe, 在此特表示感 谢。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同意我在本文中的总体 观点,本文文责自负。
[2] 艺术家宋冬参加与在北京太庙展出的展览(后 因故取消)的题目叫"是我"(It is
Me),宋 冬参展的录像作品使用太庙的柱子作为投影 屏幕,通过将他、他父亲,和二者的重叠影像 分别投射到三根不同的柱子上,这件作品述 及父 子关系这一当代中国艺术的敏感话题。 详见下文。
[3] 吴文光本人并不将他的纪录片称为"先锋电 影",关于"先锋电影"的命名问题我们将在 下文讨论。 [4]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称谓是在新闻网络上, 在芝 加哥大学回答提问时,吴文光本人使用了这个 英文词(Master),他说"He is the
master.I am a small guy." 证明新闻媒体并没有错误理 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5] 这样的镜头我们在吴文光的另一部短片中也
可以见到。当吴文光在一个下雪的冬日前往 观看被取消的"是我"展览时,包括他在内 的大多数观众并不知道这次展览已被取消。 他用摄像机拍下了他所目击的一切。在这次 芝加哥大学展览中,这部经过剪辑的短片被 作为展览的一部分放映)。
[6] 按照吴文光在芝大回答问题时的解释,"江湖"
通常给人带来"江湖险恶"、"江湖上又出事 了"之类的联想,语涉一个民间社会。可是, 如果稍加反思,我们不难发现,"跑江湖"通常 并不是江湖艺人的自说自谓,"江湖"一词的 语义演变,从"永忆江湖悲白发"(李商隐)到 《江湖奇侠传》(平江不肖生)到《笑傲江湖》 (金庸),从来都不是一种自下而上(从民间到 知识分子)的渗透。恰恰相反,现代汉语中"江 湖"脱离了它在古汉语中最普泛平实的语义 (江与湖,意谓人生旅途),成为一个文学趣味 很浓的词汇。
[7] 电影工业依赖于其它艺术门类,成功地"复原" 出"过去中国"的摄影(电影)影像(photogr aphic
images,笔者使用这个词以区别于那 些传统的中国视觉艺术,如中国山水画,所制 作的影像),并非张艺谋的发明。在重看《末 代皇帝》时,我惊讶地发现有若干片断,比如 戴连枷的几名妇女在故宫外徘徊的镜头,居 然是丝毫不差地仿自一套在西方广为人知的 老照片,而我从前却从来不曾注意过这些镜头 的涵义。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证明,视觉 的真实并非总是直接来自客观现实,而对于视 觉真实的解释是可以存在文化差异的。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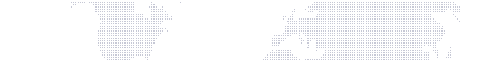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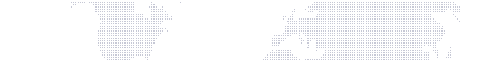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