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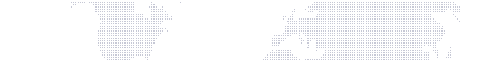
| | 网站首页 | 文章中心 | 学术动态 | 资料下载 | 建议留言 | 文化论坛 | 学人博客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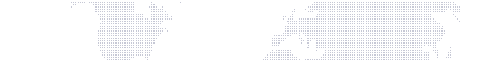 |
| 您现在的位置: 文化中国 >> 文章中心 >> 文学研究 >> 文学理论 >> 文章正文 |
|
|||||
| 《文心雕龍‧原道》“天地之心”義的啟示 | |||||
| 作者:鄧國光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5-21 | |||||
|
【提 要】本文就〈原道〉文本探明其核心主張和主體意志的內在關係,突顯《文心雕龍》的文學性。〈原道〉標題的“原”,是從〈序志〉的“為文用心”立義。〈原道〉中“道”和“天地”互文,是等值的意義符號。道即天地,反之亦然。劉勰沿傳統的思維定勢,以“天地”為“為文用心”的對象,視此心為“立言”的主宰。人文化成為“立言"的祈向,劉勰以一套聖人以文立極而垂不朽的寓言和譜系,自證刻下立言的事業的莊嚴。“天地之心”飽含劉勰用世的懷抱不能得暢的寄懷,不是空泛的理論語,和〈序志〉的垂夢互文。“垂文"的用心在〈程器〉顯豁,體現於《文心雕龍》為一貫而博大的人生信念。 【關鍵詞】道 天地 文 心 立言 言與世界的關係,是一種類推關係,而不是指稱關係;或者還不如說,複製功能是重叠在一起的;語言談論天和地,語言在自身最始形態的結構中複製一縱一橫的十字,並宣稱其將降臨──而這十字架反自我確立。 福柯《詞與物》[1] 道與天地 〈原道〉起筆頌讚“文”:“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2]標題雖然是“道”,但正文的重心在“文”,開筆彰然入目的“文”,冒起全篇。 先在“天地”義說起。 《易傳》強調“天地之大德曰生”[3],天地之義,大哉偉矣。《易傳》彰明天地生生之德,立意崇高,充滿愛惜和尊重生命的情懷,其人文精神的光輝,千古不磨。劉勰在《易傳》天地大德義再翻一層,以“文”之一義融攝“生”之德,“文”的色彩世界自生生的過程中自然呈現出來,則“文”是天地之文、生命之文。《文心雕龍》所說的天地,“文”是呈現的德;《易傳》所言的“天地”,“生”是作用之德。“天地”各有義屬,再不是客觀世界的天地。客觀的“天地”何曾表明“生”是自我的作用?亦何曾標示“文”是自我的呈現?“生”之與“文”,俱人賦予“天地”的意義;古代文家有“一字立骨”法。《易傳》以“生”、《文心雕龍》以“文”,為“天地”立骨。此可視為作文之道,然客觀的“天地”何嘗具此骨骸?《易傳》所談的“天地",自非客觀的“天地",而是義理的天地,乃具備特殊義涵的文字符號。 在經驗而言,天舉首可見,地,腳踏即感,一上一下,實實在在,根本毋須贅說,亦不煩理論的推究。但“天地”何故在《易傳》和《文心雕龍》以“生”、“文”符號化呢?二十世紀中葉卡西爾的“符號活動”(Symbolic activity)提供了深入思考的平臺: 人是在不斷地與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應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圍在語言的形成、藝術的想象、神話的符號,以及宗教的儀式之間,以致除非憑借這些人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見或認識任何東西。人在理論領域中的這種狀況同樣也表現在實踐領域。即使在實踐領域,人也並不生活在一個鐵板事實的世界之中,並不是根據他的直接需要和意願而生活,而是生活在想像的激情之中,生活在希望與恐懼、幻覺與醒悟、空想與夢想之中。[4] 不論現實生活或者是上層建築的一切領域,人類都在作繭自縛,以自我衍生的意識和相對應的符號“翻譯”世界[5],並以“翻譯本”解讀真實的世界。在符號世界的基礎上,福柯進一步指出:“語言與世界的關係,是一種類推關係,而不是指稱關係。”[6]於是語言所塑造的世界,意義存在於自我,因為語言所陳述的意義,與物自身並不相干,而語言的意義只是陳述者自身的感覺或想像的一個綜合體而已。根據卡西爾和福柯的符號詮解,同一“天地”,《易傳》以“生”為德,而《文心雕龍》以“文”為德之所以然,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同一對象的兩種翻譯本,而可說是有意的“誤讀”[7]。《易傳》的“生”義於自身的文本具足;同理,《文心雕龍》的“文”義亦構成完整的意義體系,本身具足,儘管話語辭彙淵源於《易傳》,但不等於說〈原道〉是《易傳》的義疏和翻版,因為〈原道〉的意義指向及《文心雕龍》全書的理論架構,都是特殊和具創意的。《文心雕龍》引用《易傳》為主要學術資源的精心營構的“文”論,並不影響《文心雕龍》的獨創性,正如卡西爾之不足左右福柯。劉勰的刻意涵攝《易傳》,顯然易見。“文”之融攝“生”義,便是推陳出新的“誤讀”創造。 既彰明“文之為德”的符號涵義,接著申明“道”的意義及其在〈原道〉文本所處的地位。 〈原道〉既明白以“道”為題,“文之為德”自然與此“道”相配。道和德的互配關係,是秦、漢道家的基本話語,兩者亦構成道家譯述宇宙圖式的基本框架[8]。即使於字面上而言,題目亦自然聯繫到秦、漢道家的著述:《文子》和《淮南子》。《文子》的篇首是〈道原〉,《淮南子》的第一篇為〈原道〉。《文子‧道原》全文敷衍老子“道”的特質和作用,其後篇章,有〈道德〉、〈上德〉、〈下德〉,皆申述老子的話語以掊擊時局人心,再陳述“治國”的理想方略。[9]至於《淮南子》開篇〈原道〉,接下來是〈俶真〉、〈天文〉、〈地形〉、〈時則〉等,基本上是老子義的闡述,強調“道”的形上的根本意義;高誘注訓解〈原道〉的篇義說:“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10]《文子》、《淮南子》都刻意突顯“道”的根本性,發揮老子“道”先於“天地”的觀念。“德”只是後屬者,先“道”後“德”,是道家的基本思路,《文心雕龍‧原道》強調的是“道”、“德”並生,全文的敘寫重心在“文”義的德;把“道”等同於“天地”;就這犖犖兩大處而言,已足見劉勰刻意擺落道家的“道德”觀。視天地為“道”的自身,屬《易傳》一脈的思維。故此,望文生義,比傅於道家之學,或以道家為“體”,必致扞格。 《易傳》所論皆天地內事,不涉天地之外,這是因為《易經》六十四卦,乾、坤二卦包籠其餘六十二卦,顯示發生在天地之間的一切變化和可能。〈繫辭〉起筆申明“天尊地卑”,乾、坤因而定位,“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11];強調“《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12],宣稱《易》“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13];《易》義體現於天地之間,說:“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14],而天地亦盡其為大,“廣大配天地”[15]、“法象莫大夫天地”[16]。〈繫辭〉突出的是“天地變化,聖人效之”[17];不獨《十翼》的〈繫辭〉以“天地”為理論的大框架,其他篇章亦同樣本此“天地”之義立說,論及“道”的問題,都是在“天地”的場景之中展開,跟道家置“道”於“天地”之上的思路是有所不同的。〈說卦〉的“兼三才而兩之”說[18],表明《易》有天、地、人三道,而道不出天、地、人之外或之上別有一高懸的道。〈文言〉的“合德”說[19],強調天地間一切意義俱能在“大人”再現。而〈彖〉、〈象〉無不以“天地”的恢宏場景中展示“人道”。於《易傳》的文本世界,不存在抽象的、高懸的“道”,而“天地”一義充分符號化,為鉅大義理場的背景。 《易傳》本“天地”義開展“人文化成”的論題,這種思路,於先秦儒家習以為常。《荀子‧禮論》的“三本”,便提出:“天地者,生之本也。”[20]和《易傳》“天地之大德曰生”相通。人處天地間襄贊天地生生之德,是謂參天地,具言之是謂“人文化成”,於是人以“參天地”的絕大功德,方可同儕“天地”,而得以合稱“三才”。這種參天地的人文化成之功,於《禮記》多所展示。〈禮運〉、〈中庸〉、〈孔子閒居〉諸篇有所論列[21],均闡明“天地”為教化的本原。這些原本天地以化成天下的禮樂制作,稱為“人文”,是聖人“立人極”的不朽業績。《荀子》、《禮記》等先秦儒家一脈,均於“天地”之中追溯文明的根本。 劉勰在〈原道〉所開展的論述,歸本於天地。〈原道〉的“天地”具符號意義,其意義在自身符號世界之中。客觀的天地稱為“自然界”。《易傳》、《荀子》、《禮記》、《文心雕龍》所表的是義理的宇宙,即符號化了的“天地”,若以“自然界”的天地視之,便理路扞格了。在先秦儒家符號化的義理言,“天地”是上下兩極,是絕對的存在;“天地”之間的一切生命活動和形態,統稱“物類群生”,皆出於天地的交互作用。現代所遣“自然界”一詞,是謂“宇宙間生物和非生物的總和,即整個物質世界”[22],除非現代論著所用的“自然界”義別有屬,則詞義是十分清晰的。如果把“自然界”放在先秦以迄《文心雕龍》的義理場之中,其不等如“天地”,顯然易見。而“自然界”於這套義理場,亦只屬“天地”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群生物類”,是“天地”所生,寓“天地”之內,屬於“天地”而不能等同“天地”。因此,以“自然界”意義的“自然”解釋《文心雕龍》的“天地”義,則劉勰所開出的義理,便頓失根本。至於〈原道〉提及“自然之道”和“夫豈外飾,蓋自然矣”,都不是“自然界”意義的自然,那是指不假外力的自發呈現,“就是自然而然的道理”[23],即現象和本質之間的應對關係。這種應對關係,劉勰至為重視,“文之為德”,正是“道”的對應自身呈現;這一“自然”,說明“文”的必然屬性,而非“自然界”義涵的自然。〈序卦傳〉所說的“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24],符號化的“天地”,是符號化的生命大原。 “道”於漢代訓詁,是指直通一處目的地的大路[25],意義的指向,在“行”的動作,而不在路的自身。先秦以來,各家所陳述的義理旨在指導現實生活的“行”,都稱為“道”。因此,“道”之一詞並非一家一派所獨佔尊享,運用“道”字陳述義理,不必一定道家。道是必由的大路,在文字運用的過程中亦自然稟受了恒常、普遍,和到達幸福的彼岸的涵義,這涵義令以“道”自表的義理系統,自信是千古不磨的“真理”。於是,凡言“道”,皆不離“可以實現的永恒真理”的潛在意義。“道”的是否“真實”,均不在乎,正如“天地”一詞,又何嘗是指真實的天地!葛瑞漢很深刻指出: 中國思想家孜孜於探知怎樣生活,怎樣治理社會,以及在先秦末葉怎樣證明人類社會與自然宇宙的關聯。至於何為真實、何為存在,眼睛可睹,耳朵可聞,觸覺可感,又何問題之有?(中略)對中國人而言,探尋“多”後的“一”的目的,不是為了發現某種比映現於感官的表象更為真實的東西,而旨在發現在各種不斷變化與相互衝突的生命與統治之道背後的常道,而對立學派都把各自的道說成是聖人之“道”。即使界限問題未能解決那又何妨?[26] 這是說,“道”不是終極的關心對象,而是實現“道”之外的某種目的的途轍。前述《文子‧道原》、《淮南子‧原道》,其敘述重心是“治國”,其“道”是如何有效的治國。同理,《文心雕龍‧原道》非探求“道”的自身,關心的重點,是總冒全篇的一個“文”字。這個“道”是展示“文”的永恒根源,這根源是絕對的存在,毋需任何說明。那麼,《文心雕龍‧原道》的“道”,指的是甚麼呢?答案是:“天地”。 經《易傳》符號化了的“天地”,具有永恒、廣大、生化、變動等意義元素,與“道”的符號意義相通;天地與道互換,兩者的義涵相同,兩者可以說是等值的。《文心雕龍》以“道”概指天地,便是等值的互換。因適應駢文的行文習慣[27],顧及句子字數的匹配和規定,互文是普遍應用的行文方式。因此,“道”與“天地”互文的情況,可透過文意解讀顯示。〈原道〉起筆: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 道和德相配立義,“天地”即等同於“道”。於是可以讀為:“與道並生者,何哉。”而起筆用“天地”一詞而不用“道”,正緣於題目用“原道”,以互文見巧之故。 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 玄黃是天地的象徵色彩,方圓是天地的象徵形態;以天地的色彩和形態,張開起筆的文勢,開展以下迤邐表敘天地之“文”: 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 此寫天象之“文”。 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文。 此表地之“文”。 此蓋道之文也。 此收束;“道之文”攝“天地”之文。以此一意義段作為後文解讀的標準,“天地之心”是為“道心”,文意自顯。具言之,“原道”即“原天地”,〈序志〉自述謂“本乎道”,即本乎天地。劉勰立義本來明確。就〈原道〉互文修辭考察,可以確切肯定“道”等同“天地”。 然而,劉勰著力闡述的,不是這“道”或“天地”,而是與“道”並生的“德”,即大寫的“文”。[28]如前分析,“道”的本身是甚麼的問題,在中國思想史的大傳統來說,並不重要,關鍵在循行於“道”所應完成的目標。劉勰身處這大傳統之中,對“道”本身不著筆墨,亦是必然,這不表示劉勰有意立異或突破。同理,與“道”互文的“天地”,其自身亦非關注的重點,若從〈原道〉本文尋求義涵,則頂多以“日月”代表天,而“山川”代表地,都不具備更豐富的意義,就是“日月”、“山川”四個基本的象形字而已。劉勰詮表的,是“天地”的功能,是“道”之“德”,這便是“文”。 這思維定勢決定了取證的途徑,不是於現實世界中尋求客觀的立論理據,而是在符號系統中自我證明。這符號系統便是《易傳》。在《周易》六十四卦之中,首兩卦是代表天的乾及代表地的坤,只有這兩卦才附上〈文言〉。所以〈原道〉很強調這點,說: 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符號的自證,猶本文開端所引福柯的話語:“這十字架反透過《聖經》自我確立。” 道心與垂文 《文心雕龍》所遣用的“文”一字的義涵,涵攝甚廣[29],總一切現象、形態、色彩、聲音等凡感覺所能觸及的,都納入“文”的範圍;在符號意義上說,“文”和“現象”義無所別。這一“現象”和“天地”與生俱來,是自然呈現;則“現象”的本質,亦與“天地”或“道”相同,既元始同來,舉首可見,身體可感受,真實性跟“天地”沒有分別;即使給符號化了,也不必在現實世界中尋求存在的翻譯說明,亦同樣在《易傳》這整存的符號世界進行自證。〈原道〉特表“傍及萬品,動植皆文”,乃表述一“事實”:充盈“天地"之間的一切事物都是“文”。劉勰並非論證或考究,只迻寫“事實”。他沒有絲毫的懷疑和揀別,絕對肯定“文”就是一切,包括“天地”、“萬品”,人固然不在話下,即使生命本能的性情也是“文”。在他眼中,宇宙就是一個“文”。對“文”如此執著的肯定,不是源自事實的考察或義理的推敲,卻是根源於孩童時代的一個夢。劉勰於〈序志〉自表說: 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 稱之為實錄不如視之為“寓言”。上攀青天,採摘絢麗的雲彩;這和“夸父逐追日”的寓言,沒有本質上的分別,只是故事的主角不同而已。“攀而採之”是劉勰“寓言”的意旨。《文心雕龍》的“天地"是斑爛瑰麗的色彩世界,這世界是“真實”的。劉勰就是把攀採美麗的“技術”,無隱、無私的向後世宣述,並鼓勵後人努力營構那絢麗的世界。 正因如此,〈原道〉全文雖然以“文”為標誌,但文意的歸向,淌流有在,朝向“心”的一義[30]。在〈原道〉中,心是主宰一切意識的根源,是天地的中樞。“有心之器”四字,是劉勰所強調的,緣此四字,人才能夠同處於永恒的天地,而得以秀出天地間的眾物。〈易傳〉謂“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之為天地,既屬形而上的抽象符號,相對於實在的世界,則是虛的。“有心之器”乃形而下,是具體的、實存的。形而下的“心”和形上的“道”,關係是如此緊密,相輔相成,甚至衍出“天地之心”,即“道心”,而形上和形下的閡隔,完全打開,以經學術語稱述,是謂“旁通”[31]。旁通無滯,是劉勰嚮往的精神境界。天地人之相通,全賴此“心”;故此心是人心,亦同時是天地之心,乃就作用說,而非生理實相的心臟。此道心是不斷發生作用,故亦同天地之常存。常存永恒的道心乃薪火相傳的精神感召,因此,乃是超越個體生命限度,並存於人類文化的歷史長河。基於道心的特徵,劉勰表詮道心之際,亦順成此內在理路,先陳述道心的作用,次陳道心的承傳。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是作用;這作用不假他力,自然而然;而這作用是普遍性的,不是特殊事例,乃有發生在一切人身上的可能,故以“道”稱。道者人人可循由的大路。合而言之,便是“自然之道”。心為言的主宰,文以言而得大耀光彩。文的根本是心。因此,“有心之器”的人,是文的傳遞者。人運用言所制的文,乃是自然而然,稱之為“人文”。人的本質德性,稟受於天地。 “天地"有其開始,是為“太極”。太極是“天地"元始,即“道"的元始,這只是概念的存在,而非實有。太極本身是概念,不必符號化。符號化乃針對實存事物,以自我意念翻譯原物,並取代原物在真實中的地位。“天地"、“道"則是實存物的符號。田此,太極是太極,道是道,兩者不相混。〈易傳〉謂“太極生兩儀”,兩儀若是指“天地",則是道生於太極。此純粹是概念上的衍生意義,若比類以求,太極還同樣有其元始[32],層層上推,沒完沒了,便淪為文字遊戲。因此,〈原道〉所說“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只是運用〈易傳〉的現成話語敘述人之文與道並生的概念,無意在“天地"之上再凌架一個太極,節外生枝。 劉勰早已肯定“天地"以及萬物其自身均呈現文,這一個“文”字的符號義,是客觀存在的,即使沒有人類,宇宙萬物的文亦自存。就此一種對人的意識之外的世界的肯定和表述,已顯示劉勰執筆之際,根本不存在佛教心識和緣起性空的觀念。而且,對心外的世界如此執著和肯定,頌贊的是三才之美,可見《文心雕龍》和佛學思維,根本是無從契入的。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劉勰又極重視由心所展現的人文的立人極的作用,傳遞〈賁卦〉的〈彖辭〉的話語:“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突出主體的心的轉化作用。劉勰表述人文,實涵蓋兩層意義:其一,由心至言,由言至文,是自然而然,基本上屬本能範疇。其二,人文的有益於人世,則必須在本能的基礎上,刻意講求,方可能成就經天緯地的立人極事業。劉勰著力表述的是第二義。這“用世”之信念,是從“生”為“天地"的大德的《易》義開出。 劉勰“經天緯地”的用世情懷,可從刻意表襮的第二個夢說起。〈序志〉敘: 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 如七歲時發的採雲夢,這三十歲所起的夢,夢境是如此清晰,立意是如此俊爽磊落,不啻是異代傳心,直接追隨孔子的步武,以教化行於中國。若說孔子垂夢這件事,是實錄,還不如看為“寓言”;一則精心營構,寄寓人生的追求的“寓言”。這則“寓言”於《文心雕龍》太重要了,正是因為孔子的垂夢,使這位三十歲出頭的士子,明確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亦悟出生存在世的人生價值。孔子自表的“三十而立”,深透後人骨髓。三十歲已經可以頂天立地,可以建立“事業”(《易》的事業)的基礎,奈何已屆而立之年的劉勰,不但沉淪下僚,連成家的機會都不可能[33]。要建立人極“事業”,必須擠入政治制度的中樞;於六朝的門弟社會,劉勰的出身已決定其終生不能如願[34]。退求其次,修文用遠,注經則前修的成就已經高不可踰,於是在“經典支條”的“文章之用”上,補償一生的遺憾[35]。這則孔子垂夢的“寓言” 雖然表面上以熾熱的讚頌筆調宣達出來,但接下來的敘寫,交代到撰作《文心雕龍》的動機之際,表明自己以文辭為用的信念,便泛起了兩種情緒,一顯一隱。其顯見的是於“寓言”之中獨得孔子的鍾愛所牽動的強烈用世情懷,於是泛起的立人極的“教化主”的意識,整頓“訛濫”的“文體”。這種高昂的“教化主”的壯志,自然予後人產生“唱高調”的感覺[36],這主要是文化上以及人生觀上的時空差異造成的理解或同情的距離。在劉勰來說,這種高昂的抱負則是安身立命的歸宿;孔子垂夢的“寓言”是多麼的莊嚴和神聖,與七歲時發夢登天採摘雲霓的情景的率性任情、無拘無束,對比是如此之強烈!但三十歲的人生已身不由己,縱然一心“隨仲尼而南行”,但現實的處境已難容悉性之好,退而修撰《文心雕龍》已經是劉勰在實現自身生命意義的最後選擇。孔子垂夢的“寓言”實隱藏身處亂世的士人的無奈傷感。《論語》記載孔子一則十分傷感的自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漢代孔安國從另一面解讀:“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37]孔子夢周公,從《呂氏春秋》以來,不斷被用為話題,漢人王符《潛夫論》解讀這件事,特別強調孔子所處的時代環境,說:“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之德,夜即夢之。”[38]這些習見的文獻材料,劉勰亦必親見。劉勰夢見孔子,無疑是在孔子夢周公的基礎上所結撰的“寓言”;“甚矣吾衰矣”和“生於亂世”這類鼻酸文字,令孔子的周公之夢(不管有發與否)塗上一層傷感的色彩,而翻版的劉勰之夢孔子(也不管是否真實),正明示“欲行其(孔子)道”,但結果也同樣是“甚矣吾衰矣”,真是千古同歎!劉勰越頌美孔子,更加惹來生不逢時的深沉無奈。完成《文心雕龍》後,劉勰最終皈依,徹底放下了對經天緯地的執著。 理解劉勰的孔子夢是必要的,因為這是《文心雕龍》的精神支柱,〈序志〉強調“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其“用心”的本然力量就是來自孔子的經世精神。〈原道〉中的心義,亦必須結合這“為文用心”的深層精神,方能透徹理解。孔子的經世事業,若據《左傳》文本,謂“三不朽”,即立德、立功和立言,其輕重順次第,“立言”最後,惟依然是不朽長存之業。劉勰正實踐立言以正人極的不朽事業,〈序志〉說:“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籍孟子“余豈好辯哉”這句傳誦的話語,為自己從事於“立言”尋求客觀的認同。於是,〈原道〉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三者的文字敘述關係說,是自然而然的;但就這三種敘述對象而言,心生和文明是因果,“因"之能轉化為“果",有待“言立”,則“言立”便不是自然而然的了。人皆有心,心是不容懷疑的客觀存在。言立則文明,反之亦然。文之明有待言之立。立是功夫、是自覺,人生下來亦不能一下子直立;言雖然是本能,不經自覺的鍛煉,也不可能“立”;自覺的功夫從心上來,這種自覺稱為“心生”。由生而立,由立而明,全在功夫上說,絕非唾手可得或不慮而致。於是〈原道〉表述的是:生何種心,立何種言,便明何種道。若泛生的是聖人經天緯地的絕大事業的雄心壯志,則所立的言自然是經天緯地之言,所明的文也就是經天緯地、雄博絕麗的文。所以,存“天地"之心,便發為“天地"之文。“天地"之心是謂道心,“天地"之文乃道之文,都是永存天壤的大美;劉勰便是從這道思路肯定了立言不朽的真實性,彰明立言與行道同功。 劉勰為了證明這信念的真實性,特別表述了一套完整的“文明”史作為實據。這套“文明”史是在〈易傳〉的《易》史敘述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同樣庖犧為始,孔子為集大成。劉勰突出是“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集中顯示這些異代傳心的聖人,都在立人極的悲憫用心上用功夫;而聖人之言所以成博大精深“文”,是因為體存了“天地之心”。劉勰接著以極絢麗而鏗鏘的筆調,頌揚堯、舜、禹、文王、周公逮至孔子等聖人,以文辭為功的光輝和偉大。聖人用文辭表見天地之德,以遂立人極的生生的事業,所以最後歸結為“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劉勰〈原道〉的“文明”史,無疑是為自己的立言尋求精神上的慰藉。在熱情地營構“寓言”期間,於遙遠的古代尋求精神上的依傍和支持,可見劉勰身處現世的孤寂,慼然可感。這種對“不朽”事業的宣達,透露其失意牢落。 劉勰在〈程器〉流露“發憤著書”的衷情[39],强調“丈夫學文”,必須“達於政事”,“立言”以求用世,是人文化成的實現;然後以酣暢的筆墨,宣示懷抱: 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梗楠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耽介的〈程器〉張開〈原道〉的“天地之心”的實在意義。雖然,這段文字未臻宋儒“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精粹,但精神的向度是一致的,都是為天下蒼生謀求最大的幸福;而“窮則獨善以垂文”雖用孟子語而翻出更積極的人生態度;孟子只要求“窮則獨善其身”,但劉勰不惟不肯退縮,還希求“垂文”,繼續不朽的事業。“垂文”這兩個字,交代了撰寫《文心雕龍》的心事。以“文”垂諸不朽,與天地同存。〈原道〉“道沿聖以垂文”,“垂文”是不得已的抉擇,是遭際窮蹇,方獨善垂文;然“垂文”之功,卻懸諸日月,筆底就是乾坤壯氣,故謂“聖因文以明道”。〈原道〉這些都不是蹈空的話語,著實有著劉勰躁動不已的心緒。現實的世界杆格難通,劉勰惟有在符號的天地,任意馳騁,盡解胸中萬古之愁。〈原道〉的“道”是符號的天地,〈程器〉的“器”是自家實在的心,這刻意的安排,巧妙地結合成“道心”,首尾一以貫之[40]。劉勰之撰《文心雕龍》正是卡西爾所說的“跟自身打交道”,而《文心雕龍》的文學性便是如此產生。 結 論 因此,《文心雕龍》不獨是闡述如何“立言”的學術著作,也是劉勰述志抒情的篇章。儘管談“天”說“地”,但終歸要回到作者內心。理論或符號都是人為的,人方才是主體,心便是主體的靈魂。“原道”立意,強調此心本“天地”,立言本此心,此心為立極。〈原道〉為“樞紐”的基礎,此心正是〈序志〉的“為文用心”;“樞紐”,實賴此“用心”,此“用心”為極至,故稱樞紐。而這一“用心”,灌注了劉勰的生命體會和懷抱,是全幅而實在的。 劉勰刻意彰顯文采充盈的美豔天地,亦刻意塑造立人極的文明史,於是宇宙間上下縱橫、古往今來,“文”均在其中流動。這種“天地”為本的文學觀,為文學開闢偌大無比而又豐富多姿的“天地”;東漢、魏、晉以來越演越烈的內斂自顧的時代思潮,所凝塑的狹隘文學精神空間,從個體哀樂的自表,移向一寬廣無垠的世界。〈原道〉不是說教,而是翻出“文心”的根源:皇天后土的莊嚴華美,是文學生命的“樂土”。 《文心雕龍》體大思精,其敘述架構的系統性、理論的自足性而言,難見其匹。關鍵是劉勰是以“天地之心”書寫這部傑作。“天地”何其大,亦何其美;“體大”乃因“天地”之博大,“思精”則是“天地之心”的高明。本“天地”立文心,雖胎息於西晉的摯虞[41],惟至劉勰才大暢其義;《文心雕龍》以海涵地負的雄厚氣魄,盡攬一切文字制作,自〈明詩〉以至〈雜文〉,以彰顯文辭的秀彩;亦盡攝一切文術,以豁露立言的規矩。綜有形的文體(雕龍之謂)及內在的文術(文心之謂)於一編,籠罩傳世的文論,務為折中,不囿限於一塗。則劉勰的“垂文”,“歷史"已足證其不朽。 劉勰以“天地之心”為摧化劑,再現天人同和的文采美,為現今在二十世紀解構大潮中盡喪的文化之美的頹垣敗瓦枯骨朽骸之中[42],重建文化的尊嚴和人文之美,彰顯“天地”生生的大德,提供了範例。用“文”於“軍國”,體現“觀天文以成化”的仁德,實踐“教化”的雄偉工程的信念,本身便是復歸自我的過程[43],加達默爾強調“教化"完善自身,“一切東西都保存了"[44]。劉勰視“文"是天地一切“存在"的必然屬性,也是人及其社會的稟賦;則劉勰垂文行道,以“教化"為鵠的,追求“天地"大美,保存自身一切美好的稟賦。道德是文章,文章也是道德;道德是生命之美,文章也是生命的色彩,蘊含生命的大美;天地之文也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則是自我價值的實現的主宰根源。於是,立天地之心是在自己心靈重新展現一個恢宏而充滿生機和盼望的瑰麗文學世界。可以預見廿一世紀的全球“詩學”,張揚“天地”之美的《文心雕龍》將以“經典(Canon)”的身份,開拓“詩學”的視野,亦同時透亮“詩學"的主體精神;“天地之心"闡明:宇宙的絢麗多姿有賴於開放而負責任的心靈。 A Disclosur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Mind of Heaven and Earth in Yuen-Dao in Wen Xie Diao Lung Tang Kwok-kwong
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the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e advocation and the will of Liu Xie based on the text of Yuen Dao, and points out the situation of discourse of text. The Paper also examines out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Dao and Tien-di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emantic exchange between these two terms. Liu Xie followed the great tradition of Chinese Thought in pursue of the realm of Wen by the Way of Dao, that was Tien-di and vice versa. Tien-di was the Semantic Situation for constructing of Wen. Motivation and Will dominated the setting of personal Discourse. Liu Xie wrote a serial of a histrograph of Sages to highlight the Will of Sages that benefits the elernity and universal function of Discourse of Dao, proving the Dignity of his last choice of Cultural Calling by self. Mind of Tien-di was not a theorical term in surface. Indead it was a passion expression for Lie Xie, synchronizing the Dreams recorded in the Afterword. Thus, Wen Xie Diao Lung can be treated as literary work.
Keywords: Dao,Tien-di,Wen,Xie,Li-yan. [1] 引文見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第二章〈世界的平鋪直敘〉,黃偉民據1966年法文本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頁51。按:引用的譯文由筆者據原本稍作處理,與黃偉民的譯文有細微差別,然文意仍一致。 [2] 本文徵引《文心雕龍》各篇文字,大抵根本於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至於個別文辭,則參酌近廿年來諸家校讀的成果。凡引文但取文字,標點則不相襲。 [3] 《繫辭(下)》。北京,北京大學正體字《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周易正義》卷八,2000年,頁349。張少康教授強調劉勰對“道”的看法是“繼承和發展了荀子和《易傳》的思想”(《文心雕龍新探》,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頁29。),追溯其歷史淵源,是很實在的探索。又張立文〈試論《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影響〉,載其《周易與文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強調〈原道〉用《周易》的創作之例,不少“帶有“神話”性質的“傳說””“不宜信為信史”(頁105)。按:本文用卡西爾的寓言觀念,詮釋這些“不宜信為信史”的“歷史”的性質,處理深層的義涵,而非停留於辭彙的表象。 [4] 卡西爾(Ernst Alfred Cassirer, 1874~1945)於臨終前一年以英文發表的《人論》(An Essay on Man),甘陽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3年。上篇“人是甚麼”,頁41。按:《人論》是對殘暴的極權政治生態下人性被完全扭曲的剖白,把世界符號化,亦同時是思想主體消解橫逆強暴的途徑。 [5] 莫蘭(Edgar Morin)《複雜思想:自覺的科學》(陳一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強調:“人類精神並不反映世界,它只是通過整個神經——腦系統翻譯這個世界·····我們的思想不是現實的反映,而是現實的翻譯。這個翻譯採取了神話、宗教、意識形態、理論等形式。”(頁110)莫蘭的“翻譯論”更準確描述解說世界的概念的形成過程,有效補充卡西爾和福柯的詮釋。本文“翻譯”一詞源此。 [6] 見前揭《詞與物》,頁51。 [7] 經典的強大成就為後繼者帶來深層焦慮,於經典的影子下推陳出新或者點鐵成金式的創造性承傳,稱誤讀(Misreading)。詳見布魯姆(Harold Bloom)《誤讀圖示》(A Map of Misreading),朱立元、陳克明譯。台北:駱駝出版社,1992年。 [8]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謂:“老子修道德。”又載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謂莊子“本歸於老子之言”,“以明老子之術”。(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六十三。台北:宏業書局,1979年。頁833、834。) [9] 王利器《文子義疏·序》徵引《韓非子·內儲說(上篇)》“齊王問於文子:治國何如?”(《文子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6。)則《文子》之論道德,較老子更貼近現實的政治操作。 [10] 何寧《淮南子集釋》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 [11] 見前揭《周易正義》卷八。頁302。 [12] 前揭書。頁312。 [13] 前揭書。頁321。 [14] 前揭書。頁322。 [15] 前揭書。頁321。 [16] 前揭書。頁340。 [17] 前揭書。頁341。 [18] 〈說卦傳〉謂:“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他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前揭《周易正義》卷九。頁383。) [19] 〈乾·文言〉釋“大人”之義,發揮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前揭《周易正義》卷一。頁270) [20] 王先謙《荀子集解》卷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349。按:“三本”是指天地、先祖和君師。 [21] 饒宗頤教授〈《文心雕龍·原道篇》疏〉已把相關的文獻材料注明,可參。今收入《文轍》,台北:學生書局,1991年。頁392。 [22] 見《現代漢語詞典》。香港:中華書局,1977年。頁1369。 [23] 詹瑛先生《文心雕龍義證》釋“自然之道”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7。 [24] 前揭《周易正義》卷九。頁394。 [25] 許慎《說文解字》釋“道”字謂:“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段玉裁《注》解釋:“《毛傳》每云:“行,道也。”道者人所行,故謂之行。道之引伸為道理,亦為引道(導)。”(《說文解》卷二(下))。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頁76。 [26] 葛瑞漢(Augus C. Graham, 1919~1991)《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Disputers of the Tao: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張海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頁259。 [27]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s)稱這種行文習慣為“話語機器”。詳見所著〈劉勰與話語機器〉,載《他山的石頭記》,田曉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20至137。文章認為劉勰《文心雕龍》的表述受制於這種“話語機器”,以致不能暢所欲言,又或辭不達意,又或言溢於意。 [28] 石家宜教授〈為甚麼要對《文心雕龍》進行系統研究〉強調劉勰從“本體”意義論“道”,“把“文”說成是作為宇宙本體的“道”之“文”,“道”是本體,“文”是外觀,明顯是為了 突出“文”的地位,因為它是“道之文”,就把“文”的地位抬到不能再高的位置上,完全是為了弘揚“文”的需要。”(見《《文心雕龍》的系統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56。)按:儘管跟哲學上的本體論不侔,此處所遣的“本體”一詞是根源、根本或本質的意思,但結論是實在的,亦逗出〈原道〉的宗旨。 [29] 羅宗強教授《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第七章〈劉勰的文學思想〉強調:“劉勰是大文化的背景上著眼,來論述文體和文術的,他的“文”的概念,實際上包含了廣義和狹義的多層意思。自廣義言之,他所說的“文”,是指一切事物的文采……自天地萬物之“文”,進而論文化,也就“人文”……這個文化的“文”,包籠範圍極廣,舉凡禮制、文章、學門、言辭文采等等,無不包括在內,……自此一文化意義上的“文”,才引伸與縮小到“文章”上來,這便《文心》一書中狹義的“文”。……既包括文學,也包括非文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263。)羅教授的說明,已無謄義了。 [30] 先秦儒、道兩家俱置“心”於極關鍵的位置。詳參史華滋(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5。P184-185。 [31] “旁通”見〈文言〉,謂:“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旁讀為“溥”,是普遍廣大的意思,見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旁通情也”條。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道光七年本,1985年。頁55。 [32] 《周易乾鑿度》在太極之上,復加上太易、太初、太始、太素。見張惠言《周易鄭氏學》所輯錄鄭玄注的徵引。上海:上海書店影印學海堂《皇清經解》刊本,1988年。頁109。 [33] 楊明照先生〈《梁書·劉勰傳》箋注〉斷言劉勰不婚娶,非史傳所載的家貧原因,乃因“信佛”。收入《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391。按:此無涉於《文心雕龍》,兩可不妨。 [34] 劉勰的“士族”出身,詳見周紹恒〈劉勰出身庶族說商兌〉,收入《文心雕龍散論及其他》(增訂本)。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頁1~20。按:門弟指士族的等位。九品等位低者為寒門,劉勰出身屬此。參見張少康教授〈劉勰為甚麼要依沙門僧祐?──讀《梁書·劉勰傳》札記〉(載《北京大學學報》1981年6期,及楊明教授《劉勰評傳》第一章(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6。) [35] 周勳初教授〈劉勰的兩個夢〉及楊明教授《劉勰評傳》於這個問題,已經詳述,可參。 [36] 宇文所安《中國文論》(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第五章〈劉勰的《文心雕龍》〉,王柏華、陶慶梅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頁308。 [37] 包咸《論語集解》注引。見程樹德《論語集釋》卷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442。 [38] 王符《潛夫論》之〈夢列〉第二十八。汪繼培《箋》本。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315。 [39] 紀昀眉批“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句,說“觀此一篇,彥和亦發憤而著書者”(引自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香港:中華書局,1973年。頁427。)紀批亦有所見,惟隨文批述,難貫穴全書。祖保泉先生《文心雕龍解說》強調把〈原道〉和〈程器〉參照,說“把《文心》的首篇〈原道〉和結尾的〈程器〉聯繫起來看,似乎有體用結合的特點。”(頁986)這確是有得之言。 [40] 紀昀批〈程器〉說:“此篇於文外,補修行立功,制作之體乃更完密。”(見前揭王叔琳引,頁428。)按:紀昀不悟“垂文”是劉勰的自述,所以視〈程器〉為論“文”之外的補筆。紀昀已屬通達,尚有此惑,劉勰說的“文情難鑒”,實非虛言。 [41] 摯虞《文章流別集》謂:“夫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見《藝文類聚》卷五十六。拙著《摯虞研究》有述。香港:學衡出版社,1990年。頁184。)“上下之象”乃指“天地”之象。摯虞亦擷《易傳》話語論文,但明而未融,惟首之功不可沒而已。〈原道〉有得於《文章流別集》,亦昭然可見。 [42] 參見范曾先生〈毋忘眾芳之所在〉,收入《抱沖齋藝史叢談》。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3~34。范論與徐復觀先生《中國藝術精神》不謀而合,都在“現象學的還原”的基礎上顯豁文學藝術的主體存在及其主宰性,這也是本文論述的哲學理路。 [43] 加達默爾(Hans Georg Gadamer)視“教化”(Bildung)是“返回自身”的過程,見《詮釋學I--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Hermeneutik I -- 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u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洪漢鼎譯。參第一部份。台北:時報文化,1993年。頁25。 [44] 前揭書。頁21。 |
|||||
| 文章录入:okuc 责任编辑:okuc | |||||
|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
| 最新热点 | 最新推荐 | 相关文章 |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管理登录 | | |
 |
粤ICP备05083455号 Copyright 2004-2005 CulChina.Net 主办:深圳大学文学院·传媒与文化研究中心 站长:孙海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