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分析社会公正时,个人的利益,也就是个人有实质性的自由去选择她或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
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贫困必需被视为是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
低下,这是判别贫困的标准。能力贫困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对收入缺乏显然是贫困的最重要的原因的
观点的丝毫否定,因为收入缺乏可能是对一个人能力剥夺的首要原因。
实际上,收入不足是生活贫困的重要初始条件。如果接受这个结论的话,那么为什么要从能力
的角度来看待贫困问题呢(相对于按照基于收入贫困评价的标准做法)?我想,倾向于从能力途径
来研究贫困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 )从能力剥夺角度可以对贫困进行很好的鉴别;这种方法关注本质上重要的剥夺(与低收入
不同,低收入仅仅是工具性的显著)。
2 )能力剥夺(或者说是真正贫困)的影响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重要(收入并不是表征能力的
唯一工具)。
3 )收入低和能力低之间的工具性联系在不同的社会甚至在不同的家庭和不同个人之间都是不
同的(收入对能力的影响是偶然的和有条件的)。
第三点原因在总结和评价旨在降低不平等和减少贫困的公共行动时尤其重要。已经有很多文献
讨论了条件变量变化的不同结果,有必要强调其中的一些结论,特别是与实际的政策制订相关的部
分。
首先,收入和能力之间的关系受到年龄(例如,老人和很年幼的人有特别的要求)、性别和社
会责任(例如,女性怀孕的特别责任以及风俗习惯决定的家庭责任)、地理位置(例如,容易遭受
洪水或干旱的地区,或是城市某些地区生活不安全或易发生暴力)、流行疾病(例如,某些地方性
的疾病)和其它无法控制(或只能够有限控制)的变量的强烈影响。通过将人群按照年龄、性别、
地理位置等因素进行对比,发现这些参数是特别重要的。
第二,在(1 )收入剥夺!猠privation )与(2 )将收入转化为功能(functionings)过程
中的劣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coupling)。诸如年龄、残疾和疾病等障碍,降低了一个人
获得收入的能力。但是这些障碍还使他们更加难以将收入转变成功能,因为一个更老、更缺乏能力、
或者是有更严重的疾病的人需要更多的收入(需要补助、弥补、治疗)来实现相同的功能(即使目
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表明从更显著的角度看,“真实贫困”(即能力剥夺)比从收入纬度显
现出来的更加强烈。这一点在评价援助老人和其它除了收入低下,还有“转化”(conversion)困
难的群体的公共行动时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家庭内的分配使收入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如果家庭收入不成比例地被某些家庭
成员而不是另一些成员(例如,家庭资源配置存在系统性的“男孩优先”)使用,那么对被忽视成
员(在上述例子中的女孩)的剥夺就不能够用在家庭收入的影响充分解释。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个
很实际的问题;在亚洲和北部非洲的许多国家性别偏见家庭资源配置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从能力剥
夺(更高的死亡率、发病率、营养不良、缺乏医疗等)的角度分析比基于收入分析更容易发现女孩
遭受的剥夺。
这个问题在欧洲和北美的不平衡和贫困问题中显然不是主要问题,但是在“西方”国家中社会
基本层面不存在性别不平等的假设(通常是隐含地做出),在某些情况下是有问题的。例如,与标
准国民账户分析包括的中被承认的劳动相比,意大利是女性劳动“未获承认”的比例最高的国家之
一。统计成就和所花费的时间,以及自由的相对减少,甚至在分析欧洲和北美的贫困时都是有作用
的。对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在于公共政策有关的研究中,家庭内收入分配都是重要的问题。
第四,收入的相对贫困可能会产生能力的绝对剥夺。即使按照国际标准绝对收入是高的,在富
裕国家中相对贫穷仍然可能是能力的巨大障碍。在一个富裕的国家,需要更多的收入来购买足够的
商品达到相同的社会功能(functioning )。此项研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776 页]中
最先指出)确实是贫困的社会学研究的中心,W.G.Runciman、Peter Townsend等研究者曾分析过此
问题。
例如,一些群体在“参与社会生活”中经历的困难在某些“社会排斥”(exclusion )研究中
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参与社会生活的需要可能会导致对现代化设备(电视、录像带、汽车等)的需
求,在这些设备非常普遍(与相对不富足的国家的需求不同)的国家,这就增加了富裕国家中相对
贫穷的人们的压力,即使他们的收入比不富裕国家中的人要高。实际上,发达国家中(甚至在美国)
荒谬的饥饿现象部分原因就在于对这些消费的竞争性需求。
贫困分析的能力角度通过将基本的注意力从中间变量(means )(通常给与特别关注的最常用
的中间变量就是收入)转移到人们希望实现的最终目标(ends),相应地,或者说是转移到实现这
些最终目标的自由,从而加深了对贫困和剥夺的特征和原因的理解。这里列举的经过简单考虑的例
子说明了对基础扩展的结论的附加洞察。从更基本的层次来看待剥夺——更接近以社会公正的信息
需求的角度,使能力贫困视角更加中肯。
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尽管从概念上将贫困定义为能力不足而不是收入低下是非常重要的,二者
之间仍然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为收入是能力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典型的,较强的引导生活
的能力有助于增强一个人的能力使其更有生产力,并获得更高的收入,我们可以预期存在从能力提
高到更强的获取收入本领的途径,而不仅仅存在另一条途径。
这一种途径对于消除收入贫困特别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更好的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直接提
高了生活的质量;它们还提高了一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使其免于收入贫困。越好的基础教育和卫
生保健,潜在的穷人就越可能有较好的机会脱离贫困。
这种途径的重要性在我和Jean Dreze最近的关于印度经济改革的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关注点。
经济改革为印度人民打开了许多经济机会,这些机会在过去被过多的管制抑制并遭到所谓的
“许可统治”限制。然而把握新的可能性的机会不是独立于印度社会各阶层所做的社会准备的。尽
管改革是迟到的,但是如果社会设置能够为社会所有阶层提供经济机会的话,改革可能会更加富有
生产力。
实际上,许多亚洲经济体——首先是日本,接下来是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然后是迅速
改革的中国和泰国以及其他一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他们改革显著的特点是在完全支持的社会背
景中扩大经济机会,包括高的识字、计数和基础教育水平;普遍的卫生保健;彻底的土地改革;等
等。
经济开放的经验和贸易的重要性比其它的实现相同的提升经济的途径更容易为印度所学习。
当然,印度在人类发展方面高度不平衡,某些地区(最典型的如喀拉拉邦)教育、卫生保健和
土地改革的水平都比其他地区(最典型的是Bihar ,Utter Pradesh ,Rajasthan 和Madhya Pradesh)
要高。在不同的邦限制模式各有不同。喀拉拉邦直到最近执行的仍然是反市场(anti-market )
的政策,他们对基于市场的没有控制的经济存在深深的疑虑。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没有得到充分
的使用,在更具互补性的经济策略条件下效果会更好,现在才开始尝试这种策略。另一方面,尽管
控制程度和基于市场的机会不同,北方的一些邦经历的是低水平的社会发展。在减少不平衡时,恰
当互补性的需求是非常强的。
很有意义的是,尽管经济增长的纪录比较温和,喀拉拉邦在减少收入贫困方面比印度的其他邦
速度更快。其他的邦通过高速经济增长来降低收入贫困(Punjab是最典型的例子),喀拉拉邦则是
依赖于基础教育、卫生保健方面的进步和更平等的土地分配成功地减少了贫困。
尽管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值得强调的,仍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收入贫困的
降低本身可能并不是反贫困政策的最终目标。将贫困单纯地看作收入剥夺,并用是否能够很好地降
低收入贫困,作为评价对教育、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投资标准,这种看法是危险的,因为它混淆了目
的和手段。最基本的问题促使我们将贫困和剥夺从人们真实经历的生活和他们确实享有的自由的角
度来理解。人类能力的提高直接符合这个基本结论。人类能力的提高也可以扩大生产能力和获取收
入的能力。这种关系建立了一种重要的联系,通过能力提高有助于直接的或是间接地使人们生活富
足并使对人类的剥夺越来越少的发生。这种工具性的联系,尽管很重要,还是不能够替代对于贫困
的本质和特点的基本理解。
什么样的不平等?
处理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将会遇到很多矛盾。实质性的不平等通常很难用关于“公正”
的模型来辩解。亚当·斯密的关心穷人的观点与他的“公正的旁观者”的视角相关。类似地,
JohnRawls 的关于“正义和公平”的观点是:基于“原始状态”,也就是人们不知道他们将会成为
什么样的人,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种观点提供了对平等的更为丰富的理解。从社会实际成
员的合理性来看,社会安排中的特权不平等也是很难捍卫的(例如,在这种不平等条件下,其他人
“不能够合理地被拒绝”:Thomas Scanlon提出并使用的道德评价标准)。当然,严重的不平等不
具有社会吸引力,有些人可能认为,严重的不平等就是野蛮。更进一步,对不平等的感受可能会腐
蚀社会凝聚力,某些型式的不平等可能使得社会效率很难实现。
在许多情况下,试图彻底根除不平等可能会导致巨大的损失——有时候甚至损失全部。这种冲
突是温和还是剧烈依赖于具体的情况。关于公正的模型(包括“公平的旁观者”、或者是“原始状
态”、或者是无理由拒绝)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些不同的因素。
毫不奇怪,总量和分配之间的冲突在经济学家中受到了大量的专业关注,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
问题,所以这是理所当然的。通过同时考虑总量和分配问题来评估社会成就,他们提出了许多妥协
的规则。一个很好的例子是A.B.Atkinsons 的“平等分配的等值收入”(equally distributed equivalent
income ),他的概念是在估计总收入的实际价值时,要根据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来调整,这样
就可以将总量与分配因素之间的替代关系转换为反映我们伦理判断的参数选择。
然而,冲突程度的不同与选择的“纬度”有关(或者说是与分析和考察的具体核心变量有关)。
收入不平等可以完全分解为其他“纬度”(其他的相关变量)的不平等,例如福利、自由和不
同方面的生活质量(包括健康和长寿)。甚至,总体上的成就也可以看成是不同纬度的综合(例如,
按照平均收入来对社会进行排序与按照平均健康状况进行排序的结果是不同的)。
收入和能力两个不同视角之间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分析不平等和效率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一个
收入很高但是没有机会参与政治的人,从通常的角度来看不是穷人,但是却缺乏一项很重要的自由。
一个比绝大部分人都富裕、却生了一种需要昂贵的花费来治疗的疾病的人,即使在通常的收入
分配统计中他也不会被认为是贫困的,但是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来说他显然遭到了剥夺。一个失业
但是获得了政府救济(此为失业的利益)的人,从收入的角度比从拥有一份可以自我实现的工作的
宝贵机会角度看遭受的剥夺要少的多。因为失业问题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现在的欧洲)是非常
重要的,这是另一个在不平等分析中对收入和能力视角之间差异的把握有很强的需要的领域。
失业和能力剥夺从收入角度和那些与重要能力相关的角度对不平等的判断可能是很不相同的,
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一些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例子来证明。在欧洲,这种差异特别显著,因为现
在欧洲的失业非常严重。失业导致的收入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收入(包括失业救济)来补
偿,这在西欧非常典型。如果收入损失是失业造成的全部后果的话,那么这种损失就在很大程度上
被消除了。然而,如果失业对个人生活还有其他严重的影响,导致了其他类型的剥夺,那么通过收
入补偿实现的改善就是非常有限的了。大量的证据表明失业除了造成收入损失之外,还有许多更深
层次的影响,包括心理上的伤害,工作动力、经验和自信的损失,发病率(甚至死亡率)的上升,
家庭关系破裂,社会边缘化加剧以及种族矛盾和性别歧视激化。
在现在欧洲经济体出现大规模失业状况的情况下,对收入不平等的强调只能是误入歧途。实际
上,在现在这个时候欧洲大量的失业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不平等问题,与收入不平等同样重要。
过多的关注收入不平等趋向于给西欧国家以压力,使其降低本来就比美国小的多的不平等,并
避免出现美国所出现的收入不平等上升的情况。按照A.B.Atkinson,Lee Rainwater 和Timothy Smeeding
经过仔细调查作出的OECD报告的结论,实际上欧洲在不平等的水平和趋势上都有非常良好的记录。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不仅比欧洲国家要高,而且以绝大部分西欧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速度上升。
然而,如果我们把视线从收入转移到失业,情景就大不相同了。失业在许多西欧国家迅速上升,
而在美国则没有这种趋势。例如在1965-1973 年期间,美国的失业率是4.5%,而意大利是5.8%,法
国是2.3%,西德则低于1%. 而现在欧洲三个国家(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失业率都在10%-12% 之
间,美国则仍然在4%-5% 之间。如果存在失业冲击的话,那么在经济不平等的分析中就应该包括失
业。收入不平等的趋势使得欧洲有了自鸣得意的理由,如果不平等的领域更加宽广的话,那么这种
自满可能是很深的误导。
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对比关系到另一个很有意义的(有时是更加普遍性的)问题。美国社会的道
德规范对贫穷和困顿缺乏支持,而作为典型的福利国家的西欧国家,对此难以接受。与此同时,美
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发现在欧洲很普遍的高达两位数的失业,是确实难以忍受的。欧洲则非常平静的
继续接受工作缺乏(及其进一步缺乏)。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在于对于社会和个人责任的观念的差
异,下面我将进一步探讨。
卫生保健与死亡率:美国和欧洲的社会观念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的不平等近来颇受关注。例如,
从收入的角度,非洲裔美国人显然比美国白人低。这通常被认为是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受到相对剥
夺的例子,但是这没有和世界上其它的穷人相比。实际上,与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相比,非洲裔美
国人在收入方面可能要高很多倍,即使是考虑了价格差异之后依然如此。从国际角度来看,对美国
黑人的剥夺似乎是并不显著的。
但是收入是进行比较的正确角度吗?活到成年,而不会在未成年之前死亡的基本能力是否重要?
按照这个标准,非洲裔美国人比非常穷的生活在中国、印度喀拉拉邦、以及斯里兰卡、哥斯达
黎加、牙买加和许多其他穷国的人要差得多。有人认为非洲裔美国人过高的死亡率主要体现在男性,
特别是年轻男性身上,其原因在于暴力的流行。因暴力而死亡在年轻黑人男性中确实很高,但并不
是问题的全部答案。实际上,在这方面黑人女性不仅比美国白人女性要差,还比印度喀拉拉邦的女
性差,也略差于中国女性。尽管因为暴力而死亡的状况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过去几年,与中国人
和印度人相比,美国黑人男性在死亡率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除了暴力死亡原因之外,还需要提供
更多的解释。
实际上,即使我们研究更高年龄的群体(在三十五岁到六十四岁之间),证据表明与白人男性
相比,黑人男性的死亡率也明显要高得多,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相比也是如此。即使按照收入差异
进行调整,这种差距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实际上,一项对1980年代的详细的医学研究表明,即使经
过收入差异调整,黑人与白人之间女性死亡率差异仍然非常大。在此项研究中发现,美国黑人男性
的死亡率是白人男性的1.8 倍,而黑人女性的死亡率大约是白人女性的3 倍。经过家庭收入调整之
后,黑人男性死亡率是白人男性的1.2 倍,而女性则高达白人女性的2.2 倍。这表明即使完全考虑
收入水平的原因,在今天的美国黑人女性在年轻时死亡的概率也远远高于白人女性。
将我们的信息基础从收入扩展到基本能力,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不平等和贫困的更全面的理解。
当我们关注就业的能力和在工作中取得相应利益的能力,欧洲的状况看起来就确实很糟糕,而
当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关注转到生存能力,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就显得特别严重。与这些差异相关的
有关政策背后,在大西洋两岸对社会和个人责任方面的观点肯定存在重大差异。在美国的政策优先
序中,为所有人提供基础卫生保健的责任很少,在美国有许多人(实际人口超过四千万)没有任何
形式的医疗保障和保险。这些未参加保险的人,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主观原因而没有参加保险,
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未参加保险的人,是因为经济状况而缺乏参加医疗保险的能力,也有一些人是
因为先前的医疗状况而被私人保险公司拒保。在欧洲,医疗保障被视为是与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无
关的基本权利,美国的状况在政治上是难以接受的。在美国对于疾病和贫穷的政府支持受到非常严
格的限制,而在欧洲这种支持是被广泛接受的,对于从卫生保健到教育等领域的公共支持的社会责
任的观点也是如此,欧洲福利国家认为这些是必需的。
另一方面,现在困扰欧洲的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在美国可能是政治炸药,因为如此高的失业率
会使人们自我实现的能力受到很大损害。我相信没有任何美国政府能够在现在失业率上升一倍的情
况下不受损害,即使失业率仍然可以保持低于现在意大利、法国或者是德国的水平。欧洲和美国各
自的政治承诺特点(或是缺点)看起来有根本上差异,而这种差异则与从某个不同的基本能力的丧
失来看待不平等的视角紧密相关。
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和剥夺现在极端贫困主要集中在世界上两个地区:南亚和撒哈拉
以南非洲。它们在所有地区中人均收入水平最低,但是仅从收入角度出发,无法得到它们在剥夺以
及相对贫困方面的全面特征和内容。如果将贫困看作对基本能力的剥夺,从世界这块土地上的生活
信息看到的还是比较明亮的图景。下面基于我和Jean Dreze合作研究,以及他的两个后续研究,尝
试作一个简明的分析。
在1991年有五十二个国家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低于六十岁,这些国家合起来总人口为16.9亿。这
些国家中有四十六个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六个国家(它们是阿富汗、柬埔寨、海地、老
挝、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也门)在这两个地区之外,而且这六个国家的总人口数仅占五十二个低预期
寿命国家总人口(16.9亿)的3.5%. 南亚除了斯里兰卡外的所有国家(即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
尼泊尔和不丹)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除了南非、津巴布韦、莱索托、博茨瓦纳以及一些小岛国(如毛
里求斯和塞舌尔)外的所有国家都属于四十六个低预期寿命国家。当然,每个国家内部状况并不相
同。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条件较好地区的人口也获得了长寿,而一些平均预期寿命非常高的国家
(例如美国)也可能有一部分人会遭遇和第三世界国家相似的生存问题。(例如,在美国纽约、旧
金山、圣路易斯和华盛顿等城市的美国黑人,其预期寿命要比六十岁低得多。)但是按照国家平均,
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确实是当今世界上寿命短、生活不安全的地区。
实际上,印度一个国家就占到所有五十二个国家总人口一半以上。它在平均水平上并不是最差
的(实际上,印度的平均预期寿命非常接近于六十岁,而且最近的统计已经超过六十岁了),但是
在印度内部生活条件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印度的某些地区(从人口上来说,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
家类似或更多)确实与实际上最差的国家类似。在预期寿命和其它指标上,印度的平均水平可能确
实要比表现最差的国家(诸如埃塞俄比亚和扎伊尔,现在叫做民主刚果共和国)要强得多,但是印
度仍然有大量地区,其预期寿命和其它基本生活条件与这些遭受剥夺最严重的国家的情况没有什么
区别。
表4.1 比较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最不发达地区和印度的婴儿死亡率和成人识字率水平。表中不仅
给出了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作为总体的这两个变量的值(第一行和最后一行),还给出了撒哈拉
以南非洲表现最差的三个国家,印度表现最差的三个邦,以及这每个邦中表现最差的地区的值。显
然撒哈拉以南(实际上在全世界也是如此)没有一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高于Orissa的Ganjam地区,
而且Rajasthan 的Barmer地区的成人女性识字率也是世界上最低的。这两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其
人口都多于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两个地区的总人口数则多于塞拉利昂、尼加拉瓜或爱尔兰。实际
上,在这些生活质量的基本指标方面,Utter Pradesh 整个邦(该邦人口与巴西或俄罗斯差不多)
也不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最糟糕的情况好多少。
如果将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来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成人识字率还是婴儿死亡
率,这两个地区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从预期寿命来看它们却是不一样的。1991年印度的预期寿
命约为六十岁,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则远远低于这个指标(平均约为五十二岁)。另一方面,强有力
的证据表明,在印度营养不良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更加严重。
表4.1 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国家(1991)
婴儿死亡率比较成人识字率比较地区人口(百万)婴儿死亡率(每1000名活产儿)地区人口
(百万)成人识字率* (女/ 男)
印度印度846.380 印度846.339/64印度“最差”的三个邦奥里萨邦31.7124 拉贾斯坦邦44.020/55Madhya
Pradesh 66.2117 比哈尔邦86.423/52Utter Pradesh 139.197Utter Pradesh 139.125/56“最差”
邦的“最差”地区Ganjam (奥里萨邦)3.2164Barmer 拉贾斯坦邦)1.48/37Tikamgarh
(Madhya Pradesh )0.9152Kishanganj (比哈尔邦)1.010/33Hardoi (Utter Pradesh )2.7129Bahraich
(Utter Pradesh )2.811/36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差”的三个国家马里8.7161布基纳法索9.210/31
莫桑比克16.1149 塞拉利昂4.312/35几内亚比绍1.0148贝宁4.817/35撒哈拉以南非洲撒哈拉以南非
洲488.9104撒哈拉以南非洲488.940/63注:非洲年龄截止点为15岁,而印度为7 岁。需要注意的是
在印度,7 岁以上识字率通常高于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例如,1981年所有7 岁以上人口识字率为
43.6% ,而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为40.8% )。 资料来源:J.Dreze 和A.Sen ,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 !
猠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从(1 )死亡率和(2 )营养的不同标准来
看,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存在不同的模式。印度在生存方面的优势不仅可以从预期寿命的比较中
得出,其它死亡率指标也得出同样结果。例如,在1991年印度死亡的年龄的中值(median age at
death )约为三十七年;与此相对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加权平均值(死亡年龄中值)仅为五年。
实际上,甚至有五个国家的死亡年龄中值低于三年。从这个角度来看,非洲的未成年死亡问题比印
度要严重得多。
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印度和非洲的营养不良情况,我们会发现不同的结果。印度营养不良的统计
结果远远高于萨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水平。在分析中我们忽略了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相比,印度的食
品是自给的。印度的自给是基于在普通的年份,国内生产供给可以很轻易地满足市场需求。但是市
场需求(基于购买力)低估了食品需要,印度实际的营养不良看起来比撒哈拉以南非洲高的多。按
照通常的标准来判断,非洲营养不良儿童的比例是20%-40% ,而印度营养不良儿童的比例高达40%-60%.
印度所有儿童的大约一半营养不良。尽管印度人比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活得更长,而且其死亡年龄中
值远远高于非洲,但是在印度营养不良儿童远远高于非洲,不仅是绝对数量高,而且占所有儿童的
比例也高。如果再加上性别歧视在印度很严重,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则轻的多,我们就可以发现印
度比非洲更不舒适。
与世界上两个最贫困的地区的各自剥夺模式的特点和复杂性相关的是非常重要的政策问题。与
撒哈拉以南非洲相比,印度在存活方面的优势与一系列导致非洲未成年人死亡的因素有关。因为国
家独立,印度就可以免于遭受饥荒和长期大规模战乱问题的影响,而这些会周期性地损害大量非洲
国家。印度的卫生保健体系,尽管很不完善,还是很少受到政治和军事骚乱的破坏。更进一步,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曾经有经济衰退的特别经历(常常与战争、社会动荡、政治动乱有关),这使它
们很难提高生活水平。两个地区相对的成功或失败的评价必须注意到它们各自发展经验中的上述特
征以及其它方面。
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都存在地区性的文盲问题——这也是一个象低
预期寿命一样,可以将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同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区分开的指标。如表4.1 所示,
两个地区的识字率非常接近。无论在印度还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年人中每隔一个就有一个是文
盲。
在比较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剥夺的特性时,我关注的三个基本能力剥夺的指标(即未成年死
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当然还不能提供这些地区能力贫困的全部图景。然而,还是能够给出迫
切需要关注的一些触目惊心的失败和至关重要的政策问题。我也没有试图对能力剥夺的各个方面进
行“加权”,得出衡量贫困的“综合”指标。在政策分析中,相比不同方面的分量指标,总量指标
更加不能引人注意。
性别不平等和失落的女性(missing women ) 现在我开始论述另一方面——性别不平等;这
一节参考了1992年出版的不列颠医疗杂志(BritishMedical Journal )中的我撰写的文章“失落
的女性”。我指的是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女性死亡率过高和人为的存活率更低的恶劣状况。这是性
别不平等原始的显然可见的方面,通常性别不平等的形式是更微妙的,其表现并不是面目可憎的。
但是除了表象之外,人为的女性更高的死亡率是对女性非常重要的能力的剥夺。
在欧洲和北美,女性的实际人口数一般比男性要高。例如,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女性与男性
的比例超过1.05. 而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情况大不相同,尤其是在亚洲和北部非洲,那里的女性
/男性比例可能会低到0.95 (埃及)、0.94(孟加拉、中国、西亚)、0.93(印度)、甚至0.90
(巴基斯坦)。在分析世界上的女性/ 男性不平等时,需要重视这种显著的差异。
实际上,在所有地方出生的男孩都多于女孩(大约多5%多一点)。但是许多证据表明,女性比
男性更加“吃苦耐劳”,并且在得到平等对待的情况下,更容易生存。(实际上,甚至女性胎儿的
存活率也要高于男性胎儿,从概念上讲男性胎儿的比例比出生时还要高。)这是从“西方”女性更
低的死亡率女性/ 男性比率高得出的。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导致了女性的这种优势。男性在过去的战
争中死亡存在一定的影响。而且一般来说,吸烟造成的影响男性更大,男性遭遇暴力死亡的可能性
也更大。但是很明显的是,如果得到平等的对待,即使排除上述原因的影响,女性人数仍然会高于
男性。
亚洲和北部非洲女性- 男性比率较低表明了社会因素的影响。很简单的计算就可以得到,如果
这些国家的女性- 男性比率与欧洲和美国相同,女性应该比现在的数目多很多(根据男性的数目可
得)。按照欧洲和美国的比率,仅中国“失落的女性”就达到5000万,将这些国家加起来,有超过
一亿的女性“失落”了。
然而,使用欧洲或美国的比率可能是不恰当的,这不仅因为战时死亡的特殊条件。因为在欧洲
和美国,女性死亡率更低,所以女性- 男性比率随年龄上升而上升。亚洲和北部非洲较低的比率可
能是由于其较低的预期寿命和较高的出生率。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不选择欧洲或美国的女性- 男性
比率作为比较基准,而选择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女性在相对死亡率方面不太具有劣势,而且那里
预期寿命不高,出生率也不低(实际上正相反)。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女性- 男性比率1.022 作为
基准(在我以前和Jean Dreze的研究中使用过),得到的估计值是在中国失落的女性为4400万,印
度3700万,这些国家的总数仍然超过一亿。
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种途径是计算如果女性在存活方面不存在劣势,按照这些国家的实际预期
寿命和实际出生率,应该有多少女性。直接计算并不容易,但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历史数据应用
人口模型,Ansley Coale进行了初步的估算,其结论是中国“失落的女性”有2900万,印度2300万,
这些国家的总数约为6000万。尽管这个数据低得多,但已经非常大了。更近一些的估算,基于更多
的历史数据,得出的失落的女性的数目要更大一些(大约9000万,由Stepuan Klasen估算) 为什
么在这些国家中女性总体死亡率高于男性呢?考察一下印度,那里的不同年龄段(age-specific)
的死亡率,女性总是高于男性,直到三十多岁。除了分娩期过高的死亡率可能使母亲死亡(在
孩子出生过程中或刚刚出生之后)以外,显然没有合理的理由解释女性在婴儿期和少年期在存活方
面的劣势。在印度除了偶尔出现的杀害女婴的不幸事件以外(即使存在这种现象,对如此大规模的
过高死亡率,以及其年龄分布,也不能给出任何解释),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对女性健康和营养
的相对忽视,特别是(但不仅是)在少年时代。实际上有大量直接的证据证明女孩在卫生、保健、
就医甚至吃饭方面受到忽视。
尽管印度的案例比其它得到了更广泛的研究(在印度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研究人员多于其它国
家),对女孩在健康和营养方面相对忽视的类似证据在其它国家同样可以找到。在中国甚至有证据
表明忽视的情况在最近几年迅速恶化,特别由于从1979年左右以来强制推行家庭计划生育(familyrestrictions )
(例如在部分地区推行只允许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以及其它改革措施。在中国还有一些新的,不
好的征兆,例如报告的新生男孩与女孩比率迅速上升,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它地方的水平。这很可
能表示“隐藏”了新生女性婴儿(为了逃避强制性的计划生育),这会导致(尽管不是真实的)较
高的女性婴儿死亡率——不管是否考虑(因为新出生和新死亡的都没有报告)。
然而,最近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该手段在中国确实很普及,家庭选择中反女性的偏见的新动
向是采用性别选择手段。
总结性评论经济学家往往被批评为过于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可能有人对此有一些怨言,但是
必须注意到在此学科的历史过程中,不平等问题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注意。亚当·斯密,他通常被
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之父”,就深刻关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那些将不平等视为公众关心的核
心问题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例如卡尔·马克思、John Stuart Mill、B.S.Rowntree 、和Hugh Dalton ),
不管他们可能是其他什么学科的学者,实质上都应当属于经济学家。近年来,在A.B.Atkinson等的
带领下,研究不平等的经济学开始繁荣起来。这并不是否认在经济学其它领域的研究中表现出来的
对效率的关注,但是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总体不应该被指责为忽视不平等。
如果说需要抱怨的话,应该是在经济学中,将研究的重点仅仅局限于非常窄的领域,即收入贫
困。这种局限的影响是忽视从其它角度看待不平等和公平,而这些方面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有深远的
影响。过度强调收入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而忽略其它变量,诸如失业、身体疾病、缺乏教育和社会
排斥等方面的剥夺,实际上扭曲了政策争论。不幸的是,将经济不平等定义为收入不平等在经济学
中确实非常普遍,而且常常认为二者实际上是同义的。如果你告诉别人说你在研究经济不平等,别
人立即就会得出结论,你是在研究收入分配。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隐含的定义在哲学作品中也可以找到。例如,著名的哲学家Harry Frankfurt ,
在他的重要论文“作为道德理想的平等”中,对“经济平均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有力的批评,
他将“经济平均主义”定义为“在金钱的分配方面不能有任何不平等的教条。”然而,收入不平等
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不同是重要的。对作为价值或目标的经济平均主义的许多批评都容易针对收入
不平等的狭义概念,而没有理解经济不平等的更广泛的概念。例如,追求收入平等的理念会反对给
予有更多需要(例如,有残疾的人)的人更大份额的收入,而按照经济平等的规则则不会反对这样
做,因为有疾病而造成的对于经济资源的更多的需要,在判断经济平等的条件中必需得到考虑。
实际上,收入不平等与其它纬度的不公平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加疏远、更具偶然性,因为经济其
它方面,比收入对个人利益(advantage )和实际自由的不平等影响更大。例如,非洲裔美国人与
更穷的中国人、印度的喀拉拉邦人相比,死亡率更高,我们发现某些因素影响的方向与收入不平等
相反,这包括带有很强经济意味的公共政策措施:卫生保健融资和保险、公共教育提供、地区安全
安排等等。
事实上,死亡率差异可以作为更深层的隔离种族、阶层和性别的不平等的指标。例如,对“失
落的女性”的估计表明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地方存在显著的女性劣势,这是其它统计不能完全体现的。
还有,因为家庭成员的收入是和其他家庭成员共享的,从收入差异角度无法分析性别不平等。
为了获得经济富裕不平等程度更清晰的观点,我们需要通常被回避了的更多的关于家庭内资源分配
的更多信息。然而,与其他的剥夺(诸如营养不足和文盲)一样,死亡率的统计可以直接提供在一
些重要的尺度上的不平等和贫困的状况。此信息也可以用来表明现存的机会不平等(获得外部收入、
入学受教育等)之外,对女性相对剥夺的存在。因此,现状分析和政策措施应该从能力剥夺的不平
等和贫困的更宽广的角度来进行。
尽管收入在个人享受的利益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收入(和其它资源)与个人成就和
自由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恒定的,也不是自动的和必然的。在收入“转化”到我们可以实现的不同
“功能”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偶然性可能导致系统性的变化,影响我们的生活模式。在本文中我已
经说明了在收入获取和实际自由(实现人们认为值得的生活方式的能力)之间可能存在系统性的变
化。个人差异、环境差异、社会风气的不同、理性偏好和家庭内分配的差异,这些因素各自的角色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
有的观点认为,不管能力是否被剥夺,收入是同质(homogeneous magnitude )的。这种鲜明
对立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收入估计都隐藏在一些特别的(通常又是重要的)
假设的国际差异背后。而且,真实收入的个人间比较并不能够提供效用的个人间比较的基础
(尽管在强制进行总体上的武断假设应用福利经济学时,这种差异通常被忽略)。为了从收入差异
的比较得出自身有价值的指标(例如幸福或自由),我们需要注意影响“转化”率的环境变化。收
入比较方法是更“实际”地获得个人间利益(advantages)差异的方法的假设是很难成立的。
更进一步,我已经表明,从公共政策优先排序(public priorities )的角度讨论不同能力的
价值的需要是一项财富,它迫使我们弄清在价值判断不能(也不应该)避免的领域,应该作出什么
样的价值判断。实际上,公众参与这些有价值的争论(不管是明确的方式还是含蓄的方式)是民主
和负责任的社会选择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共判断不能脱离公共讨论的需求。公共评价不应该
被聪明的假设所替代。某些假设通过掩饰价值判断和透明性原则,得出精细和流畅的表象。例如,
做出(通常是隐含地做出)两个需求函数相同的人在商品束与幸福度(well-being)之间必然具有
相同的关系(不顾其中一个人身患疾病而另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残疾而另一个人不是等等)的假设,
实际上就是回避考虑幸福的很多其它影响因素的需求的一种途径。正如我试图说明的那样,当我们
用其它形式的信息(包括生存和死亡因素)补充收入和商品数据时,上述这种逃避变得非常明显。
在民主的框架内,公共讨论和社会参与是政策制订的核心问题。除了具有其它职能之外,民主
特权的使用(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是经济政策制订实践本身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自由导向
的理论分析(approach)中,参与自由必然是公共政策分析的核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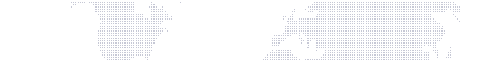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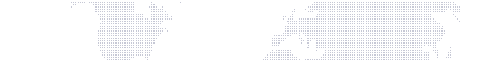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